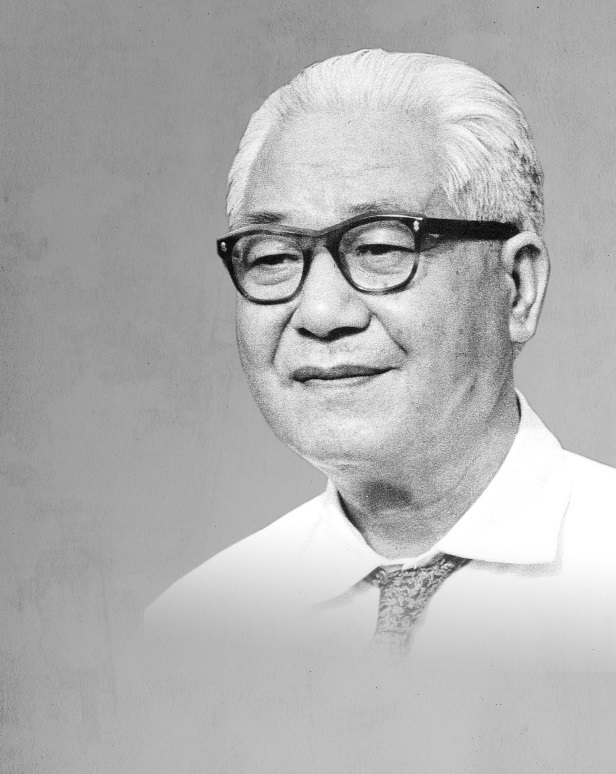
彭述之:我的一生經歷憶述 (二)
( 訪問者: 鄭致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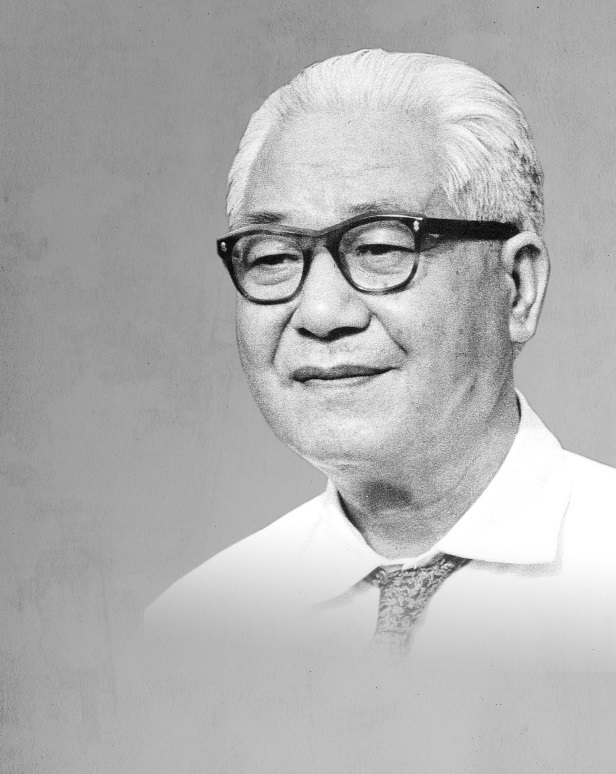
(八) 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
这是我亲身经历,也感觉很深刻的。人们对革命的热心冷下来了。由此可以知道后来苏联的官僚主义为什么抬头,托洛茨基那个反对派为什么支持的人不多。因为对世界革命十分失望。
1923年11月7日开始的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运动,是由《真理报》一篇文章引发的。
在这以前,托洛茨基的意见,尤其是关于工业化是跟斯大林不同的。托洛茨基在1923年初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剪刀差,就是城市与乡村的问题、工业与农业的问题。托洛茨基跟斯大林之间最大分歧,到了1923年11月开始,就爆发出来,非常的激烈。因为我同时是苏共党员,那时也懂俄文了,所以,我以俄国共产党党员的资格,同时是中国支部的负责人,所以我有权责去参加各种争论会。那时俄国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党内提出的不同意见还是可以讨论的。甚至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提出的一系列意见,关于工业问题、农业问题,有一些是关于党的民主问题,尤其是后一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在某些场合简直打起上来。在那时候、那种情形,我的感觉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内幕,就我个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从前都是掩藏,不让一般党员知道的,只有上层少数人知道。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这种情形,俄国人不同,尤其是年轻的人更激动。那时我们感觉到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关于老人的,所谓保守派的问题。另方面,我们对托洛茨基的一种崇拜,我们从中国到莫斯科的,脑海只认识列宁和托洛茨基二人。看文章也是看他们的,到了俄国就更是如此。无论什么地方,挂的照片都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的意见,知道他们在革命中的贡献,当然对他们有更深刻的认识了。所以,对托洛茨基、列宁是一样的,对斯大林的印象不好。社会上,对他认识不深。尤其是我听他的演说,都要打瞌睡的。听托洛茨基演说就兴奋得很。这是年青人的一种印象。
对于他们的斗争,我们觉得斯大林不对,但是还不能够辨别。很难,很不容易。比如老人跟青年,这些老人都是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干革命,崇老,所以我们对老革命家都很尊重。但同时看到年轻人很活跃,精神很好。所以,这个问题,年青人就很难了解。托洛茨基那本《新路线》,我也看了。他说,老的人会堕落,在那时候看,很难懂。当然后来懂了。那时候,我们对这些,也没有拟好一个纲领。别人也不能帮助我们。我觉得这种情形不是很好,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关于托洛茨基的意见,关于农民的剪刀差,我是完全同意的。不过老的人要腐化,变成反动,这对我是个新鲜问题。不能够了解和太难了解。当然,现在了解了。
1924年1月列宁逝世,这对俄国是很大一个冲击。因为列宁的死,这个反对派的争论就停止了。从那时候,斯大林对付托洛茨基的各种各样压迫手段开始了,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来。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月到7月召开,托洛茨基没在大会上演说,没有说话。大会上讨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德国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跟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有很大的分歧。但会上并不公开说,所以与会代表不能了解这个问题。因斯大林一个人演说,托洛茨基没有演说,就可以看出,我们已经感觉到托洛茨基受压迫。讨论德国问题最重要的是路特·费舍尔,一个女的,那是他们所谓的左派。就我看出来,当时我们感觉到的,他们这帮人支持斯大林。因为布兰德莱总书记也被撤,当作一个代罪羔羊。所以这次会议没有把德国1923年失败的责任弄清楚 。就是斯大林一贯的做法,他失败了,他不去好好弄清楚那个失败的教训。
至于中国问题、东方问题,我感觉到他们不愿意讲。东方的委员会由布哈林率领,我们有中国的代表四人,就是李大钊、彭述之等。我对这次大会没有感觉得到什么东西。不过那时候中共中央要我回国工作。
现在要谈一般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从托洛茨基主义开始到现在的情形,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九) 回国组织左派反对派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中国,主要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少数的人像陈独秀和我觉得这失败完全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错误。我们检讨教训,还没有看到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的文件,我们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已经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了。例如,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跟布哈林把反对的对方打压住,我们就觉得,这个共产国际没有希望,不能改变,所以我们拒绝开会,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态度。随后看到托洛茨基的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过去政策的基本错误,这个文件就是中国革命的总政策。另一个是第六次大会以后,有一个中国的革命问题。当时要提供一条路线,以代替斯大林的那种冒险主义,就是在反革命时代实行的政策问题。我和陈独秀看了这两个文件,我们没有犹疑就认同托洛茨基所说的,无论对过去对未来都是对的。所以决定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一个左派反对派。1929年4月间,那时另外还有一个小组织,就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一批中山大学学生。他们已经开始组织托派,但是,这批学生有个严重的缺点,这批学生从前在革命之中,没有人做过负责任工作和领导的,在1925年孙中山大学开办以后,才把他们送到莫斯科。他们没有革命经验,直接从托洛茨基的文件吸收和认识,从托派思想的拉迪克校长处受到影响,所以赞成托洛茨基思想。他们回来后,在党内没有地位和不能到党工作。就在外找少数的人组织一个团体,出版《我们的话》。这样的组织没有影响力,尤其在党内没人知道。在外也没人知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时我们还在党内的,就可见他们没有影响力。到了我们组织左派反对派时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一方面,像陈独秀和我组织反对派是在过去党内担当最高责任的领袖,党员差不多全是干部,他们当中有省委书记、中央委员。上海有批工人,曾参加党和干部组织起来的五卅运动的。像这样一个左派反对派在世界上是第一个,在当时社会上的规模大和人数众多,是最高的领导层。像美国是有加农,沙赫特曼,阿伯恩,他们曾是中央委员,但他们人数少,且从地位上来说,他们在党内没我们那样高层的地位,在社会上没我们那么大影响力,陈独秀、彭述之在革命世界中没人不认识。领导上千万工人运动,社会影响力是不同的。我们第一次签名的,就是我们的意见书,我们共有81个人,81人都是党的干部,像陈碧兰,她是上海区委的委员,也是妇女运动的领袖。所以组织了左派反对派,使整个党都震动,全中国社会上都认为是大事件,共产党分裂了。像中国著名的胡适之、大学教授们都发表了意见,我们的宣言公布后,上海《每日新闻》日本报章翻译了。日本写的中国历史还提到此事。新闻发布后,中共翻译俄文和其它文字,如法文、德文等。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第三国际,我们建立反对派,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关注。开始就呈现出与以前完全的不同。至于后来《我们的话》分裂成两派。一派是王凡西和刘仁静,他们另出版一小刊物没有影响力。他们在党内也没影响。最后他们离开党,没有在党内去影响群众。我们使整个党震动了。我们的组织是左派反对派《无产者》,《无产者》出版《我们的话》和《十月》刊物,从《我们的话》分裂出来的刘仁静办《十月》。 另外还有几个从莫斯科回来。很少人想加入我们。他们不是很好的革命家,加入我们行列还提出条件,刘渊要做中央委员。组织还没成立,谈什么中央委员?他们另外成立组织和出版《战斗》小刊物。我们主要是在党内争取干部、党内革命分子。宣言发表后,引致党内震动,三个组织召集联席会议,中央、江苏省委、地方组织和我谈话。准备开除我们。不过没莫斯科命令,他们不敢单独开除的,一定要得到莫斯科的允许。后来莫斯科的命令开除我们,因莫斯科最怕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主义是根据地方的关系,地区、省份和个人的,我们在党内领导革命运动多年,有成千干部和我们接触。革命失败后,很多干部还留在党工作,他们跟我们有接触,所以接受托洛茨基思想,组织左派反对派。因我在党内同干部接触最多,陈独秀比较少,我常到各地,上海区经常出席上海区委的会,每星期一次,和每星期出席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我常作报告。上海有上百名活动分子和我接触最广泛。在莫斯科几年,当时的干部和学生,后来在党内都变成干部领袖,我和他们关系密切。开始,我和一些老干部接触,跟他们谈托洛茨基的意见,谈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一两个月后,开始组织了几个约三四十人的小组。我们集结起来,成立一个正式组织,反对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尹宽和我。所有成员分成小组还在党内部工作,在党内也有小组,小组有斗争,说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说党的政策不对,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斗争。还在党内的干部,还不知道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组织的人,我们都接触了。陈碧兰在中学教书,她接触一批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这些人都在党内担任重要的工作,由于她接触了,所以又有一批人加入了托派,加入反对派。组织就扩大了,因此,我们办了《无产者》刊物。送给党内人看,当然外间人也看,这是秘密的,因在国民党统治底下不能公开。
随后,我们出版了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问题,除了那最初看到的两篇文外,又找到更多文章,出版一部书送给党内人看,对社会的影响更大,我们自己的组织生活正式开始。
1929年3、4月至12月,党内要开除我们。陈独秀写了政治意见书。我也写了政治意见书。尹宽也写了,还有其它的同志。他们组织特别的批判会批判我们。12月陈独秀写了最著名的《告中共党员书》。陈的档案还保存着,我的就失去了,因我几乎被捕,所有文件都丢掉。后来我们合写《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是正式宣言----81人宣言,事实是三人合写的,陈独秀、尹宽和我。这是所有托洛茨基派,苏联以外的一个最有系统的文件、最详细的文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文件,德国、苏联都没有。我们是有系统的攻击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攻击斯大林的思想和主义、官僚主义。这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个基础,应该从这开始,因为很有系统。托派的中心思想是《不断革命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阶段论,违反了不断革命论,就是我们理论上比较最高的理论基础。
1930年夏天,开始形成一些小组织。事实上除了《我们的话》在工人有地区关系如香港。上海有少数的人是党外的,都是莫斯科回来的,他们也有他们的委员会和组织,不过他们没有影响力,除了香港有少数的工人,一二工厂或船务工厂没有多大的影响。北京有些学生后来分裂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又互相斗争,最攻击的是《无产者》。尤其是《十月》社的刘仁静和王凡西说,陈独秀是过去的机会主义者,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写了文章攻击陈独秀。后来托洛茨基说:“你们应该好好向陈独秀学习”。陈独秀做反对派是执行斯大林路线的一个历史重要事件,整个共产国际内部都很重视。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内外是第一号人物,因为中国有个大革命,中国的党最大。从前一个党的领袖,加入托洛茨基运动是最伟大的一件事,证明托洛茨基思想是很有力量的,这班人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这个机会主义不是陈独秀,而是斯大林,陈独秀只是执行者。他是没有办法和必须执行,后来托洛茨基告诉他们,参加我们托派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应跟他学习。所以,托洛茨基说这个争论,这个攻击《无产者》是被党的领导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斯大林主义者利用了,在他们的干部中说:你看,托派内某些人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者,去宣传,去蒙蔽他们的干部。所以有许多老干部不满党和不满国际的斗争,像胡梦雄,罗章龙等,以前是在我们领导下工作的,我们的态度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后来瞿秋白和李立三完全是官僚主义的,对党员压迫得很厉害,不能说话,不能批评。所以,觉得陈独秀和彭述之现在组织托派是有一定道理,表示同情并参考了我们的文章后,更觉有道理,包括刘少奇等。他们称自己‘调和派’。但是托派内另一小组织攻击我们,党的领导拿去宣传,调和派便失望,给托派很大的打击,他们写信给托洛茨基,攻击「无产者」、攻击陈独秀派。所以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写一封正式信给他们,说你们应该统一起来的。同时,我们的中文宣言《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翻译成了俄文,寄给了托洛茨基。当时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对他们说,政治意见书跟托氏的意见是一样,所以你们要跟他们统一起来。由于托洛茨基这样说,这些人才放弃了他们反对「无产者」社和反对我们,才能统一。浪费了时间,同时放弃了很好的一个机会──在党内影响所谓‘调和派’。在统一当中,最坏是王凡西的一个阴谋。他想利用这个统一操纵将来的领导机关,他干了许多坏事情,陈碧兰的回忆録都批评了和斗争过。
(十)统一大会后的工作和被镇压
1931年5月开统一大会。我对统一的态度有点不同意见,统一是应该的,是托洛茨基主张的。如果不详细讨论政治和组织问题,将来又要分裂,所以我的主张跟陈独秀有点不同。我主张有一个时间讨论政治和组织问题,有了基础才统一。不过大家要统一,我不反对。所以,王凡西后来说我是反对统一的,这话不对。因这统一并不是经过认真的讨论,其实反对派内有些人是要不得的,应该淘汰的。后来有人成了叛徒和背叛了。例如梁干乔,他是《我们的话》的领袖、黄埔军校的学生,他没有要求统一,托洛茨基的信没有来之前,他是反对统一的。托的信到来,他就不敢反对了。他想在统一内做一个领袖。但统一大会后没有被选出来做成中央委员,于是统一大会后,他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梁干乔是右倾主义的具体例子,还有其它人都背叛告密了。统一会议后,所有的领导干部均被捕了。陈独秀和我也应该被捕的,我住的地方已被揭发。那天拘捕了六、七人。一位托派同志机缘巧合下得到讯息知会我,才实时离开,所有文件统统丢掉,还想方法告诉陈独秀,要陈戒严在家,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陈也没有被捕。但新选的委员会成员几乎都被捕了。那时我们是非常狼狈的!什么都丢掉了,另方面,又要想办法救援被捕的人,要找钱和关系。所以非常痛苦,陈独秀不能出门又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因为被捕,其它的,特别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人都害怕,便离开了,故此很混乱,一直到1931年8月,我们几个人都很痛苦,
到了1931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了东三省,1932年2月28日日本占领了上海,因日本侵略,中国爆发了广大的民族运动----反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人已经少,陈独秀和我及另外一位中央委员又临时组织起来,成立临时机关,我们想办法弄钱,出版周刊《热潮》,又把所有组织和党员重新组织起来,到学生和工人中活动,因有公开的刊物,可以公开办,主张言论自由,要武装抗战,支持二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本。我们的刊物有很大的影响。一般的群众和共党内部的人也看了。中共对日帝的侵略采取最荒唐的错误政策,不是抵抗日本,而是要保卫红军,拥护苏联,连二十九路军都不支持,这就是王明时代的政策。
我们编辑托洛茨基的《中国问题》和《无产者》给他们看。在战争时期,上海有几个中共支部,这个领导层看到我们的刊物了,是透过我们的同志,他们亦曾说托洛茨基的理论是对的!他们反对对托洛茨基派造谣。这时期,我个人忙得不得了,要写文,又要出席会议、支部会议、跟他们谈话,跟党的人谈话,因陈独秀不方便。他年岁大了,没有太大活力。经过很多次的谈话,把上海党部和几个淮南区的支部、沪东的和沪西的支部十几个干部,全部说服过来,变成托洛茨基派的干部。他们底下有很多任务人支部,像浦东有十几二十个工人支部的,就把最大的支部争取过来。像邮政局、烟厂、电厂等都争取过来。所以,上海托洛茨基主义就代替了斯大林主义。我们托派成功地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罢工游行。1932年10月15日我们全被捕了,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陈独秀不舒服,我代陈独秀主持会议,会议到中段,大批警员包围了,把我们六人拘捕。我们有一印刷机关,有两油印工作的也被捕了。那次被捕了约十人。陈独秀的秘书被捕了,此人叛变,被捕就供出陈独秀的地址。淮南区支部和沪东区支部的干部被捕,杨树浦区是最大的工业区,在上海东面,沪东区整个委员会被捕了。从北京来的一批托洛茨基主义者如刘家良,到上海工作也被捕了。1932年4月我们被捕到1937年战争爆发,是托洛茨基运动差不多停顿的时期。所有干部统统被捕,被捕干部有30人以上,这个打击最狠最大。在南京审判,不过审判是做宣传,所有的报章刊登我们被捕了。托派的一个工业基础,从党争取过来的,但是我们被捕了,那些干部被捕了,大家失去联系。在法庭上我很严厉的公开反对国民党。我的演说,报章摘要注销来。就是公开反对国民党,用共产主义来改变中国问题。这是一个最广大的宣传。在监狱组织了托洛茨基主义小组,常常跟他们讲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
(十一) 抗战爆发后恢复工作
从1932年被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没有中心思想情况下衰落。1937年8月的中日战争爆发,国民党不能不释放政治犯,共产党已经投向国民党。不能不释放托派,所以我们从监狱释放出来。我是最后释放的。因国民党一个领导人最仇恨我,因我在法庭攻击国民党太厉害,想把我处死。不过监狱长向司法部请示,司法部长认为不释放是不能的,最后把我释放了。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就到上海,开始要恢复组织,恢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组织,刚好有其它监狱释放来的同志,就集合讨论要恢复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又通过抗日政纲,选出执行委员会领导机关。继续出版刊物,还是秘密的,因抗日后情形稍微变化。国民党不能完全控制我们,1939年,出版公开刊物《动向》和出版托洛茨基的书,我们有一批朋友,由陈碧兰介绍我到南京结交一批朋友,这批朋友后来变成我们的同情者。 有一位曾是国民党辖下当官,很有钱的,思想左倾,到日本读书,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又一朋友是我们的老共产党员,经这朋友,他变成我们很好的同情者。另一关系,一银行家曾参加五卅运动的,他们都很同情和帮助我们。所以得到这三位朋友的帮助,出版托洛茨基的‘The Revolution Betrayed’《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名《苏联的现状与前途》)。后来又出版《俄国革命史》三大卷,是几本厚厚的巨著,还有很多小册子,也是托洛茨基写的。没有大出版商是不能出版的。像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因要翻译和校译,出版又花费很大的金钱,大出版商不愿出版没有经济效益的书籍,没有前人的经验,革命的书籍是出版不到的。所以,这几位朋友筹集资金,我们找郑超麟和王凡西翻译,给他们生活费负责翻译。翻译好就出版,很快,时间约一年多,就把托洛茨基的巨著出版了。都是朋友的帮助。
我在革命前,接触的人非常广泛,在革命失败后,有许多教授、知识分子最先离开,对这些知识分子很反感,他们从前要见我们都是见不到的,要入党不容易的,革命失败,他们最先离开。所以,革命失败后,走到另一极端,我们很孤立。被捕的时候,陈碧兰很苦,得不到帮助,只有几个老的党内的,也离开了,被捕时有第一个女儿和怀有三、四个月的身孕。我在南京跟别人不同的,我们是政治犯。我带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全是译文,有俄文的书,托洛茨基、列宁写的都有。监狱长不敢干涉我们,别人也不可以。所以有时间读书,在监狱五年,整日读书研究。什么都看,朋友来看我,问我要什么,就是书,所以朋友把各样的书送给我,我的牢房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我看列宁、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尤其看他们的通信,他们只要利用得到的人,他们就利用来帮助运动。有些人跟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跟列宁通信的并不是革命者。我觉得我们有点过分幼稚了,觉得我们孤立不对。所以要改变我的态度,不要走极端。释放后,陈碧兰介绍的朋友都跟他们见面,亦接受访问,得了一批朋友来帮助我们的运动。从这批书的发表,刊物的发表,是运动中的又一发展,从1938-1941年日本战争,珍珠港事件开始,我们的运动有新的发展,在各地方,北京、重庆、浙江、广西、把旧有关系恢复过来,有新的发展。事实上,出版一大批的书有利发展影响,我也写了一批小册子,写关于抗日的小册子,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小册子,奥地利革命失败的小册子,对托洛茨基和苏联的情况有广泛的影响,也公开出版了。
日本战争后完全变了。日本进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以,从前在租界上活动比较方便,租借是坏,但日本更坏,进入上海后,恐怖和随便捕人杀人,像希特勒进入欧洲。因此我们领导中心同各地方的关系统统断了,不能通信。随后,日本进入北京、山东、广东、广西、武汉,大半个中国都被占领了。我们的组织受到同样的压迫,加上我们在上海有五个干部被捕了,他们担任重要工作。于是,上海的组织就完全被破坏了。他们被捕,还要营救他们,我们对同志有责任的。所以,非常狼狈,幸好有些同情者,可以给他们一点钱。中国的监狱人员可以贿赂,可以找关系,所以我很狼狈,剩下的觉得上海不可留了,跑掉了,如刘家良跑到温州,其它同志都跑了。剩下几个人、陈碧兰和我,同志要求我离开上海,大部分同志可以到其它地方,但我仍留守上海。有5、6个年轻人,我把他们组织起来,开一个训练班教育他们。
这时候,大夏大学和之江大学的教授朋友,他们不大反对共产党,在革命时代是有一点同情的自由派,由朋友介绍认识,到大夏教学,之江大学原来在浙江,后来迁到上海。因我没有教育证书是不能教学的,和美国一样。我现在做教授,用我的名字没人请的。不提出哪国的学位来,是不能教学的。虽然我做过教学工作和有质素,但是不能提出来的。他说:没关系,改一个名字。我就改名陈松涛。他说,陈松涛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不过现在不愿意用他的真名字了,因日本统治有危险。校长听了后说,用真名危险,随便用什么名字。所以我就用假名陈松涛教学。
教中国通史、中国历史、有时教西洋的文学发展,又讲哲学。事实上,是讲历史唯物论。不用马克思主义名义,因为有各种学生,我是用那个意思讲马克思主义,讲中国通史、哲学、西洋文学史,有些普通学生不懂,觉得我很有学问,有左倾分子,听懂我的话,说陈教授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下课后,学生来教授休息客厅找我。“陈教授,能到你家访问吗?”我说:好的。就这样一批左倾的学生到家里来,就跟他们谈,后来争取了一大批学生,有些是斯大林派的,后来转变了,就是做教授得到的结果。
1941、42年开始,到1945年,做教授,展开同情网,结交一批同情者朋友,也是朋友介绍的,又跟他们讲马克思主义,他们是联合的和激进的,所以我结交更多的朋友,有同美国做生意的商人。这时期的我,活动范围不能到厂区,而是学生、大学生、一批自由派的、激进派的商人。这对后来很有用处,和平后,1945年8月战争停止了。同情者朋友就问,用彭述之名是有危险的。当时,写文章不能用彭述之,学术上、哲学、历史的文章用‘欧伯’。所以,同情者和自己同志叫“欧伯”,现在还是这样。他们问:“欧伯,现在和平了,战争没有了,你要做什么?想做什么?”我说,第一要出版杂志刊物。出版刊物一定要钱,他们说,事情大家商量,并筹集了十条金条,大约五、六千元。他们说,要办就办最好的。我们很快恢复组织,重新建立领导机关。因做教授,有一批学生,通过学生,又有其它革命分子,所以组织发展很顺利,有些老同志在工人中工作,1946年5月出版《求真》。《求真》是最漂亮的刊物,同情者做监督印刷,做得很漂亮,知道文章内容很好,刊物的封面也要一样的好。他做经理,把刊物办得最漂亮的。那时我忙得要命,写文和组织,还有刘家良(他后来死在越南)的帮助。我自己曾有一本《求真》,在越南丢了。我们的杂志一开始就畅销,因为水平高,不是用彭述之,用陈人白。我们的文章有水平!我们宣传托洛茨基思想,并不是拿托洛茨基的名字放在前面,内容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所以杂志影响很大,初期约4、5千份,报摊和书店可以买到,所以影响就大。随后,陈碧兰办《青年与妇女》,是她私房钱搞的。她得到一批青年人帮助,主要对青年人谈妇女问题,所以是有另外一种影响的。我们的刊物使各地方有些组织,孤立的、个别的同志,他们看《求真》,全国到处有卖,知道是老欧办的。所以他们就写信来,把全国各地方的孤立组织串连起来。个别的人写信来,也串连起来,所以很快恢复了全国组织。1948年,我们的党员团员约四十人,不过我们有很多同情者,使我们的影响更大,因《求真》是战后有名的最好杂志,连苏联大使馆也要。国民党有许多所谓左派也要杂志。所以,是托派新的发展。出版了不到三年,在1948年8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到了高点。我写了《党纲》草案,刘家良起草了《组织原则和方法》草案,在会前发给各地组织讨论,在大会上都通过了。大会通过将原来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以下简称「革共党」)。1948年,毛泽东的中共跟蒋介石的内战展开了。这时,国内局势,对托派来说,危险是一天较一天高。

(十二) 被迫南下再出国
到了1948年12月毛泽东的军队已经攻打到长江的北岸,要进攻南京了,离上海很近,我们非常受威胁。毛泽东的中共是斯大林主义的党,如果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党,没有问题,我们合作好了!斯大林主义的党特别仇视托派,可以跟任何反动派合作,就是托派不一样。故此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改变政策,否则我们全部要被毁灭或监禁,像苏联的托洛茨基运动一样,苏联没有托派存在,全部被关在集中营,所以我们开紧急会议应付时局。
中共一定胜利,因蒋介石太腐化,对中国大陆,我们采取什么立场?我们支持中共所有的革命措施,我们批判他们机会主义的政策,是我们的态度。另外,我们的党员、团员要加入共青团,加入青年团,加入工会,不能独立工作。在上海成立临时委员会,同党员联系,政治局则转移到香港去,有同志在上海出名了、许多人认识的托派要转移到其它地方,其它地方的人再调到上海,这是我们的安排。我和陈碧兰、刘家良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尹宽,他不愿意离开上海,所以他被捕了,现在还在监狱。我们到了香港,是我们不能不离开,我们一定被毁灭。毛泽东要是得到我,不会放监狱内而是要绞死的,或送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作为一个礼物。
1948年12月,我们离开上海。在广州住了个短时期,当时广州组织还有几十个人,中共的军队向广州进攻,我们只好离开广州到香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中国大陆差不多20年。同时是在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底下,托洛茨基运动是一个不同的时代。
从广州、大陆来到香港的人合起来,大约还有近一百人,我们把香港的组织推动起来,在香港出版刊物《第四国际》,我们帮助做教育工作。开始不错的,我们党员团员有学生和工人,我们帮助做教育工作,所以看来有发展的希望,但是另一件事情又来了。两个同志做印刷的被捕了。跟着,有一位姓谢的同情者是银行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人,是我们在上海影响的,他大学毕业,很有知识,英文也很好,他没有加入托派,所以他调到上海一间银行做会计主任,很高的地位。我们要接收国外报刊,我们自己地址不便,同情者说:我来给你们接收。所以他就接收《第四国际》及其它的邮件。托派中央机关到了香港,当局有侦探,也可能是斯大林党告密!香港政府是最厌恶托派的,因托派常常领导罢工,例如在船厂、大纱厂等,托派在领导,我们的同志是领袖,所以香港政府很敏感,知道我们来了,就想方法要对付,要迫害,所以花力量检查我们接收的外国邮件。有两个人被拘捕,十几人被捕了,有些释放,有些被递解出境到澳门或内地,跟着这事情发生后,他们知道彭述之在香港,他们用尽方法找我。他们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但是根据接收报刊的同情者,有时到我住的地方去,就跟踪他。警员有技术的知道他去这个地方,当局要来搜查这地方,幸好我事先知道,赶快搬到另一家去,也是朋友家。果然,一两天后,那间房子被搜查了,两同志也拘捕了。过一、两个星期,搬去另一朋友家,又有跟踪,那便衣侦探来包围,来调查,我只好又搬。大家就说,在香港是危险,连我们组织也是一个负担,所以大家建议离开香港到越南。我们的同情者是陈碧兰的亲戚,帮助筹旅费到越南去。
1950年初到越南,住了年半。因是法国殖民地,非常反动。我用假名在越南生活没问题,碧兰和我教学,我们的女儿也教学,教中学语文、中学英文。生活是可以的。1950年2、3月,越南有托派组织要到胡志明占领的越南区域去开会,刘家良也去,途中被越共拘捕,不幸死在狱中。我们又有危险了,加上北京老朋友告诉上海的同情者,说毛派知道我们在越南,要我们当心!因在越南要对付我们非常容易,只要一把手枪就可以了。越南常常打死人的。所以我们又要离开越南。香港同志给我们筹旅费,买船票到法国。到法国的时候,身上只有50美金,不过,我们希望国际上会有帮助。我们到了法国,正是第四国际召开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前,我们是六月到,七月末到八月开世界第三次大会。我是第一次直接参加国际会议,也参加了国际的领导机关。我们二十四人到欧洲,我们只有三人,有二十一人在法国。
(十三) 参与国际的领导工作
我参加了世界的托洛茨基组织领导层会议,初期还没有分裂。后来分裂了,1953年,尤其是54年分裂。我们参加美国加农所领导的反巴布洛的斗争,我们卷进去了,因为我参加国际委员会的,在国际委员会工作差不多有十年。在这时期,我是主张统一的,我还存有文件和信件。不过那时候,巴布洛派也不愿统一,英国希利也不愿统一。我在这方面跟他们斗争,要统一。到了1962年,约瑟·韩生(Joseph Hansen)来到巴黎,1962年娜塔利亚·斯道娃(Natalia Sedova)托洛茨基夫人在巴黎去世。我才第一次见到韩生。在以前,我有通信,是给加农的,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给加农,有时候是给杜勃士。我就统一的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加农,我认为要统一。在1963年韩生同劳斯·道逊(Ross Dowson加拿人),到我住处直接谈。这中间有很多的障碍,不过我是坚决要统一,后来是统一了,1963年6月在罗马开了统一会议。我是代表中国的革共党(RCP)的。陈碧兰都是国际上前线人,参加国际的领导机关工作,而且干预了国际上很大的是非问题,我们有意见,是代表中国支部的。我们对古巴,我有两个文件,还有一个是原草案。我对阿尔及利亚,写了一篇文章,是批判希利的,同时我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一些意见。在随后关于拉丁美洲的游击战争,我是单独一个人反对国际执委会的,在1968年,我们代表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干预国际托洛茨基运动。
当我们离开香港的时候,组织已受了很大的打击,多位同志几次被捕,驱逐出境。不过,他们还继续工作,继续出版文件,出版不定期的刊物,香港主要的政治意见还要靠我们帮助,我们写的文章,如我在第三次世界大会上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他们出版了,作为我们革共党的立场,此后他们对于农业集体化,也有他们出版的文章评论。1957年有一个‘大鸣大放运动’,他们也出版了文章,也有他们的立场。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有他们的意见,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关于人民公社,我是批判社工党两个领导人,史瓦贝克和佛兰克·格拉苏斯(中国名字李福仁),我是批判他们,也批判中国的苏达同志,他们都想反驳我,因此,我在1960年写了一个重要文件《关于中国局势及其政权的性质──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The Character of CCP and its Regime),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分析文件,一个纲领文件,外国都出版了,香港也出版了。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写了很多文章和访问,不过这不是我们的同志翻译出来,是明报月刊翻译出来。香港同志还出版了《向导》丛刊,不过不定期,有时几个月出一次,但是他们继续工作,还维持了一个组织。他们是不断地出版一些刊物、小册子,他们是受压迫的,双重压迫,香港政府压迫托派组织很厉害,香港斯大林派的压力。从前大陆的国民党政治机关、银行、商铺、产业,中共接收了,它有成千上万人在香港,因为有钱,工会也给他们把持了,所以斯大林派的压迫,同香港政府的压迫合起来,我们的同志简直就透不过气来。所以有些同志消极了,少数同志想做,做不出什么,就是出版文件刊物,从前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现在都50岁以上,是替我们做工作,是我们在40年代影响的,经过三十年,那时他们20岁左右,现在变成了50岁以上,也疲倦了。同时他们在香港也要生活。所以,我曾经说过:“慷慨杀身易,长期奋斗难。”我的亲身经验,一个革命者被捕了,慷慨激昂被杀不是很艰难,我们有成千的共产党员,都是慷慨杀身的,但是要长期抗争就十分难。因为革命者也是人。如果在革命过程中被捕,甚至枪毙,没什么,我自己就经历过。在南京准备死,我写信给父母和陈碧兰,说是应该做的,最后为运动牺牲,我一点没有感觉痛苦,因已决心抛出去,后来没有死,就知道革命家是艰难的。
(十四) 香港同志的处境和工作
1948年从大陆避难到香港的同志,现在算来,二十六七年了,他们在大陆,差不多都有十年历史,这些同志都经过了三十五、六年的斗争,他们要生活,又要工作,还要想方法弄钱来出版,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跟美国完全不同,比起香港同志,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很舒服了,那不能比那种艰难困苦!所以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最艰苦的。他们工作坚持到现在是很艰难的,大家认识到,那样的条件,美国现在的老同志,不过一两百人。香港一些同志,几十年了,所以我们是要体谅他们,不过我们总是要工作,这样会有冲突。我有上百封的信,我现在还保存着,加拿大有同志的信,批判他们,鼓励他们,提出建议。1968年我们到日本旅行,我和碧兰在日本住了半年,香港派同志见我们,更多知道香港的实际情形和过去十几年的情况,我们从日本回巴黎,写了一封信给全体同志,要他们积极工作,现在的世界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建议他们筹一笔款,出版书籍,出版刊物,我们说,香港的青年,请你们活跃起来,因当时欧洲和美加有个青年激进运动潮流。像美国那些年青人反越战,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筹了钱,把每月有的一点钱拿出来,筹了几千元,准备要办一个刊物,但很吃力,有钱,还要写文章。编辑的人,写文章的人不够,他们又停下来。到1970年香港出了一个新的月刊《70年代》,这月刊是香港的青年激进化运动,当然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这是一个新的青年运动,我们香港的同志很难影响他们,我们建议写的文章,他们写,但是不能够影响他们。例如王凡西,他接触他们,还不能够影响,他不能吸收任何人加入我们的运动。1972年2月间,香港《70年代》杂志二个成员到巴黎访问我们,后来又有一批十几人到来。他们一来便知道我的真名彭述之,他们是从外国的刊物上看到的。所以他们就问我许多问题。一青年李X明,第一次写信给我,说他在香港是很重要的一个负责人,我答复他许多的问题。我同这些年青人大约有一年书信往来。跟他们谈话,他们提出苏联的问题、中共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为什么苏联是一个官僚独裁的专政?为什么中共又是一个官僚独裁?所有的问题,我都给他们答复了,有时谈很长久的。最后被我说服了,他们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再进一步是托洛茨基主义。所以,这批人1973年回香港,当中著名人物是回港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革马盟)的吴仲贤,不幸中年癌疾逝世。
因年青人胆子大,他们不怕,顶多坐牢。老的同志不同,拘捕会递解出香港,到澳门或大陆去。年青人是生长在香港,英国政府不能迫使他们离开香港,最多关起他们。所以这批年青人反对香港政府,示威游行。他们敢于公开说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以,从前老同志不敢说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年青人不管,香港的报纸就知道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是这班人,报纸常常登载。从1970年开始,我们向他们建议,把托洛茨基以前的书籍重新出版,拿到书店去卖。首先拿到《七十年代》的书店寄售,它当然想卖,所以我们有一大批书,托洛茨基主义的书再版。像《俄国革命史》,像《中国革命问题》,现在又要再版。这些书籍印出来是公开卖的,所以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就扩大了。一年多两年,他们出版《十月评论》刊物。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派运动在香港等于半公开。香港政府也不像从前的压迫,共产党是公开的,为什么托派就不能公开?托派在英国是公开的,在伦敦是公开的,为什么托派在香港就不能公开。所以,我们现在的活动比较公开,半公开的,两个刊物和书籍出版。我们可以公开地代表托派去演说,由这批年青人去复兴托派运动。《十月评论》已经出版了快两年,知道他们很积极、尽力的做。我们的书现在是公开出版,《十月评论》上有我的名字,将来还有一些新出版的是我写的。他们登载我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等文章。他们要出版陈碧兰的访问记和回忆录。这就是香港现在的情形。在香港的组织有几十年,从1940 年左右,我们香港有组织,但是从来不能这样的公开,我们出版刊物,从前也有的,都是秘密的。最近一年多,我们的书公开出版,刊物公开卖。这倒是新现象,也可以表现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也是一个发展,香港的组织虽然很小,但是组织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因为所有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国家,从苏联到东欧、北韩、北越,没有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香港,我们还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而且这个组织,最有斗争的传统,这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十五) 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立场
关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我们就要检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中国大陆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对于大的事变,它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才可以判断托派起了什么作用。我们可以用几个大的事件做一个基础,做一个标准来做判断。
第一个时期是从1929年到1949年这二十年,托派活动在国民党最反动的统治底下。第二个时期,就是从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到现在二十六年。我们要分开来讲。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什么最大的事变呢?第一是‘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东北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都是大事变,对于中国的民族命运有关联。我们采取什么态度,中国怎么办?我们出版刊物,我们有文件、有宣言,我们的态度是分析日本占领中国,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政策的结果,也是第二次革命失败的结果。所以我们宣传这个基本观点。日本侵略,我们要武装对武装,应该要武装人民来对抗日本的侵略。为了这点,要求国民党应该给人民有自由,没有自由,怎能够活动呢?所以我们提出的政纲,就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这种专制独裁,只有帮助日本,因他控制了人们的自由,所以人们要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人们要有公开的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此,农民、受压迫的人们在一起,帮助农民得到自由,改善生活,因这是全民族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些自由,要有一个国民会议,要有一个普通选举的有全部权力的国民会议,把这些自由活动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纲领。我们用这个共同纲领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的专制独裁。这些纲领和宣言等,在当时都是有文件发表或登载在报章上的。
托派的运动也是上述同样的两个大时期,在上述第一个时期,首先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我们当时采取的立场,是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和武装起来抗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我们提出由国民会议来解决重大的问题。
第二是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全面进攻中国,这是继续从前占领东北三省一样,继续扩大,日本侵略是很重要的事件,对中国的国家命运很重大的一个历史性影响,同时对整个国际也是。托派的政策是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支持抗战,抵抗日本战争,就是在蒋介石领导底下,我们在军事上,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另一方面,我们批判国民党的抗战政策,是错误的反动的,它压迫人民,不许人民自动的武装,不许人民组织武装自己,自由组织,不给人民有自由,所以我们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全国人民普选出的国民会议来领导这个抗日战争。这就是我们基本的态度。我们现在看起来还是对的。后来托洛茨基也表示这个意见,与我们完全一致。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托派有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派是陈独秀,他从监狱出来,变了。在监牢,我跟他斗争,证明他的思想错误,在支持抗战行动上表现出来。他跟我们不同,他也主张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这跟我们一样,但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的抗战政策不彻底,尤其对于人民继续压迫,人民没有自由。陈独秀跟我们不同,他主张不要批判国民党,我们也无条件去批判蒋介石。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那时他已经放弃了革命的立场。他害怕批评国民党。这就是我们的文件表明的,关于陈独秀的我们有好几个决议。第二个倾向,就是托派中的郑超麟,也是个老托派同志和老党员,他是另一个极端。他因为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他说这个战争不是革命的,我们则说有进步性。他说蒋介石同日本天皇是一样的,两方面都是反动,所以他主张我们对抗战应该采取失败主义。这是极左的。这一倾向很危险,在那时候,如果在客观上,我们是拥护日本人,赞成日本侵略,因为必须首先要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他已经领导抗战,这样就等于做汉奸、做叛徒。所以我们反对,我们反对这两种倾向,我为此起草的决议案,是绝大多数同志支持的。所以托洛茨基的政策是正确的,也就是我们所代表的。后来,在日美战争发生的珍珠港事变后,王凡西又是个失败主义者,我也批判了,我们批判他,尤其刘家良最多文章批判他,他也是一种极左派。因为日本进入了中国,我们怎能够对日本战争我们要采取失败主义。我们采取失败主义等于帮助美帝国主义。对这件事情我们是正确的。有很多文件,争论得很厉害。结果,陈独秀离开了托派。王凡西和郑超麟也出来组织一个小组织。所以托派分裂了。不过,他们出去的人很少,几个人。这是第二件大事。
第三就是和平后,托派对于和平后采取什么立场?和平后,我们的政治立场是反对国民党的专政,人民要自由,我们重新提出要有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问题。《求真》同《青年与妇女》都发表这些意见,托派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

最后,是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内战,引起共产党后来夺取政权。我们起初批判共产党机会主义政策,它等于投降,在中日战争中,它投向国民党,它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这个领导,没有重要地批判,所以我们批判它。和平后,共产党还想跟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这是机会主义,和平后,情形很好,中共如果是个真正革命的党,它可以很快的发动全国的工人农民走向政权,但是要跟国民党合作,直到蒋介石把周恩来这位国共和谈代表赶走了,才逼得毛泽东增加反抗,因蒋介石已经发表宣言,要拘捕毛泽东、朱德。我们批判这些。另方面,我们攻击国民党发动内战,牺牲人民,这就是这时期我们对两方面的批判。我们主张共产党应该直接夺取政权,组织苏维埃,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国民党应该打倒的,这是我们的立场。但是在这时期,我们托派有一错误。我们的错误就是,因共产党用这样纯粹的军事手段,不发动民众,不能够得到政权,原则上是对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第二次大战后造成的整个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的局势,是非常的特殊,所以中共虽然实行机会主义,它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了政权,我们后来检讨,我们对这一点,没有估计到。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训。关于这一点我还要说的,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二十年当中,托派对于重大事变的政治态度和政策。我们现在来回顾,我们是对的。共产党就不同,是机会主义的,一时是冒险主义的,所以,这与我们不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正确,不能够成为一个群众的党,领导工农走向政权呢?这是一个历史大问题。我写了小册子解释,就是托派在国民党底下,被压迫得非常厉害,例如1932年,陈独秀和其它的同志被捕,在上海的,在全国的基础上,我们当时在城市内的基础,尤其是在上海工人中,我们可能很快的发展,成为一个大的党,但是陈独秀和我被捕,所有的干部30几人被捕,所以没有办法。这解释了托派不容易发展,是受各个时期统治者的压迫破坏太厉害。
(十六) 对中共统治政策的批评和我们的立场
第二件事,是毛泽东派走上政权后,托派的政治主张,在这点上,我们也要根据那个大的事变来看问题。起初是一般的,我们对毛泽东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我们怎么样看法?第一,他是个机会主义者,斯大林派,为什么能够夺取政权?什么样的客观原因?什么是它的主观原因?以及这个党当时的政策,它的组织上政策,它的措施,以及它的前途。最后,就是我们的态度,这必须要有一种很严肃的分析。关于这方面,我在1951年11月做了一个很认真的研究,写出了《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这是我给第四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的托派同志是完全赞同的。我在这个文件内就做了分析,认为中共能取得了政权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一是蒋介石政权的绝对腐杇无能和崩解,二是美帝最后抛弃蒋介石,三是中共力量在内战,尤其是抗战中的壮大,四是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详见十月书屋出版的《彭述之选集》第3卷)。跟着,我指出它的前途有三个,多半是东欧国家的道路,就是走向变态的工人国家,这是斯大林主义的表现。事实上,毛泽东是跟着斯大林当时的东欧国家的道路走的,我指出这个前提部份。我们的态度,我的报告后面提到,我们支持毛泽东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正确的措施,同时,我们指出他们的不够彻底,我们指出应该没收土地给农民,没收所有资本家的财产归国有,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归国有。
另一方面我们指出,工人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完全是被官僚控制,我们主张工人农民兵士都要组织苏维埃,来管理国家,然后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工农政府,工人和农民的政权,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这个态度很清楚,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这一点,我在1954年给瑞士一份托派的报章写了一篇文章,我更简约地叙述了我们托派的政治见解,在这篇给瑞士的托派刊物发表的文章中,我更具体地批判和分析,我们一方面支持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要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参加抵抗,这是我们的态度。要有一个真正的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我第一次指出,中共如果不走这条道路,而走东欧的道路,将会有一个政治革命,这是我1954年第一次提出来,是我们托派的意见。
第二件重要的事件,是共产党在1955年开始农业集体化,要农民参加生产合作社。关于农业集体化,我们支持,但是毛泽东的做法,我们反对。因他强迫农民参加。那时香港的托派同志,写文章批判这件事情。我们表示这是一种列宁对农民的态度。1957年,毛泽东发动大鸣大放运动,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一位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一方面,如果它真是要解放人民的思想自由,这是对的,但是毛泽东不是这样,他是要利用这个大鸣放来查出那些反对派,引这些反对派连同中共自己的党员说出他们的真心话,说是「引蛇出洞」,然后加以打击,当作右派,拘捕了几万人,开除了几万党员,所有批判中共的人都受打击,我们认为这是个阴谋,事实是如此。这是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第三大的事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些是中国事件中最大的事情,那时有5亿农民,要他们一下子参加公社,这使全世界都震惊了,全世界的舆论都很惊奇。因为这实在是非常重大,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但在我们托派内也有人赞成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是史瓦贝克和李福仁,中国有苏达同志是赞成的。他们支持人民公社,不加批判的拥护。那时候,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也很烦恼,形成二派,由纽约和洛杉矶两地的成员所分别代表。所以,杜勃士就要求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批评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我根据列宁、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俄国的历史事实和经验,东欧的经验,我全部的做了一个检讨,批判毛泽东的这种人民公社是一种冒险主义。我从理论上,历史的经验上,根据俄国的先例,给毛泽东一个批判,给人民公社批判。这种冒险主义必然会失败,我预先指出要失败。例如,公共食堂,我说这是行不通的,这是起码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懂得的,物质生活落后,怎能够把家庭完全不要,吃饭到公共食堂?就是美国革命以后也办不到!还要等一段时间。这是非常幼稚的,没有知识的,一定会瓦解的,公共食堂要取消的,那时还没有取消,当我说这个问题时。后来,没有公共食堂了。原来公社是一个失败,后来又恢复到生产合作社。我相信我这篇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对这个问题最精细、最正确的分析。这也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观点。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分析是有预见。对落后国家,托洛茨基主义应该研究。所以,这篇文章刊出后,把史瓦贝克和李福仁两人打垮了。所有的同志支持我们的意见,纽约的同志社工党的领导是完全支持这个见解,而且给他解除了一个麻烦困难。其它的国家,像日本的Yamayiqi,他就最赞成我这篇文章的分析。当然,没有人不赞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意见。第三件,最后的一件是文化大革命。我给中共党员的公开信,在明报月刊刊出,还有许多文章讲解文化大革命。我在1967年2月16日《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一封公开信》(见同上书)中,提出一个斗争纲领,我们的态度非常明显,我们反对毛泽东用这种办法排斥异己,排除反对派;打倒了刘少奇,林彪又来了。这就是我们正确的立场,我们批判反对派刘少奇,但是我们指出刘少奇有的政策,比毛泽东是有建设性的,代表温和改良的。我们支持这个温和派改良派,同时批判他不足够,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像我们对俄国的赫鲁晓夫批判,我们支持他的非斯大林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批判他不够彻底。最后,我们反对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的《十月评论》有大量文章评论这些事件。我分析,研究中共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关于批林批孔,是毛派的作为,涉及一些中国重大的历史问题。
对于中共这个政党和政权的分析,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共的胜利及其政权的性质──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见同上书)这是比较全面的分析。虽然不像托洛茨基写的《被背叛的革命》那样详细,不过,一般是那样一个新的分析。这也是因为史瓦贝克和李福仁,写了文章,他们认为毛的党,中共,不是斯大林党,毛的政权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权,中国实行了纯正的革命。他们是把中共美化了,这就是一种投降毛泽东主义的思想,这是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起初在社工党里,他们的文章发表使得社工党的领导层很麻烦,因为他们不很懂得中国的情形,不知道怎样答复他俩人。所以杜勃士要求我写篇文章讲解。所以我就批判史瓦贝克和李福仁,完全是根据他们的文件来批判。在托派来说,是对毛派、毛政权和托派的基本政治革命纲领的一份文件,是最基本的。我们现在根据这个纲领,视为对毛派的政治革命纲领。
总而言之,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托派文件。因它表示托派对中共的政权和前途,托派的基本的政纲,提出政治革命,表现托派是非常有原则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反对和随便赞成。像托洛茨基提出苏联要有个政治革命,他是根据理论和事实的分析,从这点上说,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继承托洛茨基。
指出托洛茨基运动在中国所经历的,这四十六年,托派对于中国问题的政治主张、政治分析是有文件写出的,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托洛茨基派有这么多的文献。因中国的事件发展得复杂,完全不同。一个斯大林党掌握了政权,又是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对整个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我们的思想贡献、正确的贡献,我认为我们是对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有人能否定我们或是有理据批判我们。此外,中国托派目前对于中国的问题是有有系统的分析,并坚持主张的。
(十七) 中国托派对几件世界大事的意见
我们中国托派对于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于世界大事的意见也有相当的贡献。例如对古巴问题,我有两个文件,1960、61年,卡斯特罗刚刚走上政权,我对他的分析。一方面,他建立的政府是革命的,但同时又有点危险,因为他国家太小和孤立。在美帝国主义压迫下,可能要堕落,尤其在苏联的援助底下会官僚主义化。我这个分析,第一次我写了篇文章,第二次,1961年我给国际委员会写了一个决议草案,我们的分析,到现在还没失效,事实上卡斯特罗是完全跟苏联走向官僚化。
第二件大事,就是阿尔及利亚,她同法国帝国主义,经过了多年的战争。我曾经发表过意见,提出阿尔及利亚应该走怎么样的道路?我这个政纲性意见包括在《白恩斯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往那里去?》一文内(见十月书屋出版的《彭述之选集》第四卷)(注)。因这篇文章提到古巴问题,提到阿尔及利亚的问题,提到统一问题,这是我对国际问题比较重要的问题的文件。我对古巴的意见又重新分析,为什么古巴走上政权和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我说得更详细。也说她的缺点。对阿尔及利亚有我提出的政治纲领。因为对阿尔及利亚,我认为,那时白恩斯是极左教派主义,所以,我就批判他。我提出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也许很重要,对于国际问题,阿尔及利亚很重要的。
[注: 该文指称 「阿尔及利亚的一切革命者必须团结起来,以现时获得的政治独立为基点,制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纲,再进而动员工人群众及一切贫苦的农民继续进行斗争,为撤退法国驻军和取消它的经济特权、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实现产业国有化、为争取工农的民主权利,和建立工农兵委员会和工农政府而斗争,以此把阿尔及利亚推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便是我们对阿尔及利亚所应采取的路线,并以此为批评本.贝拉政府一切措施的标准,和鼓励一切革命者去形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继续进行斗争的方针。」(见该书第242页)
第三件事就是关于智利1970年开始的革命,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个重要的意见。我曾经写了封信,给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我在1971年就主张智利要成立工农兵苏维埃,否则,这革命一定会失败。因为只有成立苏维埃,才能够使军队兵士,跟军官隔离起来,才能避免战争。我在《导论》中也提到。这是托派对国际运动的贡献。对于葡萄牙,我也有不同意见。我主张葡萄牙应成立工农兵苏维埃,不能专靠立宪会议。不过,这事现在还在争论。中国托派对于国际运动重要事变有其主张和分析。所以,我可以说,中国托派,从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从思想来说,是坚强的支部,我们特别的自豪。当然,我们的组织非常小,这并不是我们的主观错误,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托洛茨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有系统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不能在苏联活动,苏联的托派同志们被摧毁了。所以,我们是可以解释的。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挫折、失败,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但在政治上,是表示了托派的一种可以说是最深刻的,最广泛的意见。政治立场证明是对的,在世界的托洛茨基运动里面是不多的。
(十八) 回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
访问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第二次革命中中共宣传部的组织。当时宣传部是我负责的。在1924、25年是没有的,从前宣传部是有的,虽然没有机构,也就有个人负责,没有正式成立一个机构。我回来后,因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要我负责宣传部,所以就建立了一个宣传部的机构。是一种独立的,单独的,有一个负责人。我是宣传部部长。组织了一个宣传委员会,可以大家讨论关于宣传出版工作。因宣传部工作很广泛,要领导出版两个刊物《新青年》和《向导》,我要负责。这些刊物是对外和对内宣传。还有对内的教育工作和办党校。所以要有个宣传委员会来讨论。宣传委员会就是我、瞿秋白、蔡和森。但是蔡和森后来去了莫斯科作代表。剩下我和瞿秋白,我们宣传委员会有陈乔年秘书,我们开会讨论。有两份报纸和两刊物,我是主编,陈乔年是助手。所以,我们主要工作就是出版。有党校组织,很忙,没时间教育,因革命发展像狂风暴雨般急速!上海五百党员,连青年团员一千多些,一年后便一万多。所以我们人手不足够。教育工作做得非常不够。不过,我们也做了一点宣传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我和瞿秋白。这问题很复杂,因有许多外国书籍,老是说彭述之与瞿秋白有仇恨、有冲突。我这个人从来不同人争,我对于同志是采取一个正当的态度,我们同志间工作,政治上意见不同,也没关系,可以讨论。我是依照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我懂得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思想,我自己参加过。所以我是采取这种态度。我跟任何同志没有成见,我看他的思想,看他的工作的成绩表。对瞿秋白也是这样。瞿秋白在莫斯科有一年和我在一起,他的俄文很好,比我强,但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思想。1923年回国,和陈独秀参加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一起回来。他回来,党叫他编辑《新青年》。他写了很多文章,但是他的文章有个很大的毛病,因我也懂俄文,他把俄文翻译出来算是自己的,写上瞿秋白的名字,我看不起此事,我认为不忠实,尤为重要的,他在上海大学当教授,他讲唯物史观,他把布哈林的那本唯物史观翻译出来,后来,翻译本印刷出来写的是瞿秋白着,没有说是从布哈林的书翻译的,非常不光彩。
(编按: 原有录音带说到此为止。忆述和录音历时15天,从1976年1月1日至同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