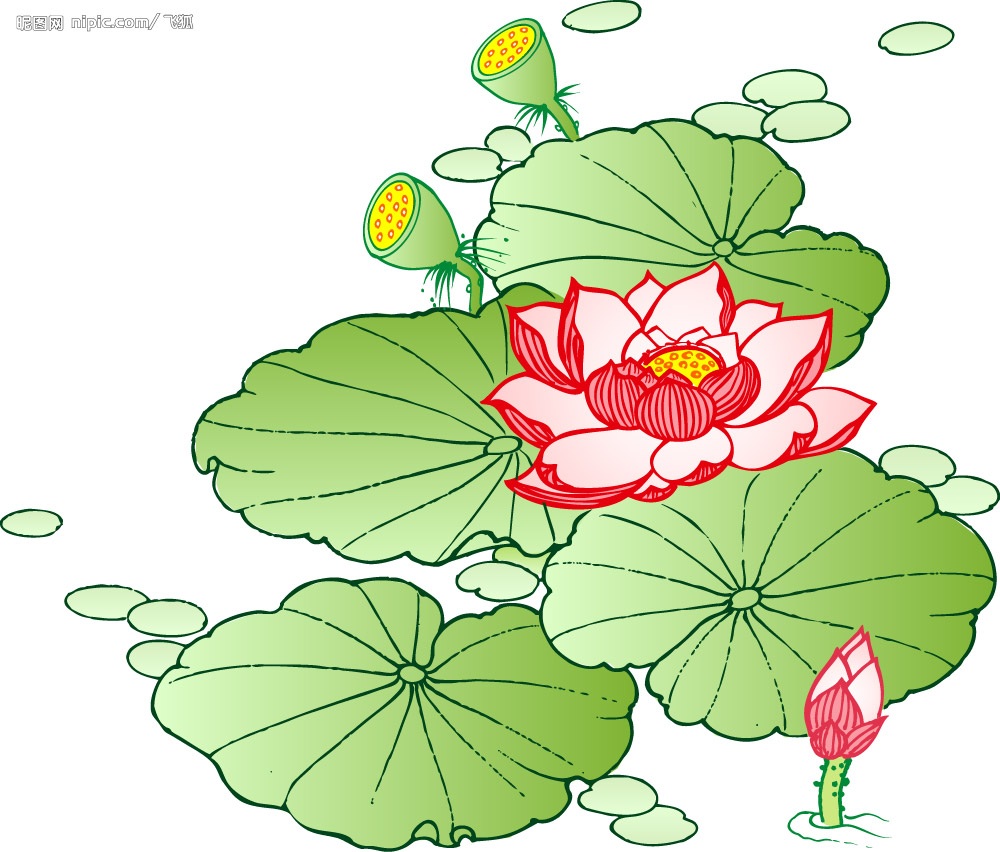我无悔!
魏帼英
我的祖父原来在湖北务农,娶妻后移居上海做小贩,卖汤丸,住在小沙渡的工人区。街上很多店铺是回教徒开的,招牌上有“清真”的字样。祖父在小沙渡工人区协助筹款创办清真寺,牲口要经他宰杀,别人称他为爸爸,意即教父。祖父生四子,我父亲是长子,我是独孩,也是五代唯一的女孩。
外祖父在农村给人家“磅牛”,拍拍牛身就能估量牛有多重,杀牛后切开来称,很准确。外祖父重男轻女,有2子2女。大舅舅帮人以马代步,是被马踢死的。小舅舅务农。
我母亲三岁时,外祖母死了,母亲哭坏了眼睛,靠比她大七岁的姐姐照顾。外祖父后来娶了填房。母亲想嫁给城里人,把眼睛医治好,嫁了比她大两岁的我的父亲,24岁时生我。父亲嫖赌饮吹,染上性病。二叔在监狱做事,把面包屑拿回家,母亲怀着我时,只吃面包屑,身体很差。祖母是出名的刻薄恶婆,经常打四个儿媳妇,母亲是她的同乡,少点挨打挨駡。据说,祖母很凶,三个小伙子都打不过她。她打骂儿媳妇后,还不让吃饭,儿媳妇之间会偷偷送饭。母亲生倒睫毛,用夹子夹着眼皮,祖母打她的时候,偏打她眼睛。我出生后,几个月打噎;祖母还好意思说,宝宝打噎,是因为在娘胎里受了气。
我是五代唯一的女孩,出生的时候,小鹅蛋脸,很美,阿訇为我洗礼时,祝贺我祖父,说你添了个天使。
我六岁的时候,祖母提出要把我送到日本纱厂筒子间做细纱童工,母亲不答应。当时,二叔是崇信纱厂的职员,在厂里有点权力,所以祖母在工厂负责派厕纸;母亲同另一人负责在打好包的纱包上盖章,活轻,下午三、四点可以下班回家。如果我做纱厂的养成工,会有工资。
母亲让我报读崇信纱厂的附属崇信小学,读到小四。我们家穷,有一个同班同学叫姚桂香,与我很要好,她和妹妹上学由家里的私人黄包车接送,路经工人房区把我接上。我读书时比较懵,小一的课文“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白布五匹六匹”,“燕子尔又来乎,旧巢破,不可居。燕子衔泥衔草,重造新巢”,我都琅琅上口,可是一本书读下来,我还搞不清“人”字原来在第一页。小三的时候开始读英文,老师问“时钟”怎么说,我答不上,后来能答是“clock”,老师问怎么拼写,我不知道,老师给我板尺,自己打手板。有一次,我问母亲拿一个铜板买英文练习本,母亲不识字,要我念英文给她听,我大声把26个英文字母念了一遍,母亲还以为我英文流利,给我铜板买练习本去。
我读书不大行,但是好奇心重,观察力强。母亲比较迷信,曾经请拖着骆驼的相士给我算命。我不迷信,自己一个人在街上观察摆地摊的相士怎样用雀鸟占卜,雀鸟会啄出客人的生肖纸片,很准确,但是我拆穿相士说,你不要指手画脚,要让雀鸟自己找。我对机器很感兴趣。大概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偷拿了叔叔的挂表,拆开来看为什么能转动,接着没法拼好,赶快把零件扔到小巷对面的楼房里,二房东知道,幸好没告诉母亲。十来岁在北方的时候,我又拆开了一个座台钟,然后重新装嵌,分针慢了15分钟,我勉强把针拨过去,没被人发现。
母亲有很强的自尊,教导我要有骨气,不贪婪,不依赖。我自小走路只往前走,目不斜视。也很执着,两条小辫子不对称,一定要重扎,否则不肯出门。母亲管教很严厉,知道我不规矩会教训我。没有玩具,我用绳子绑着一块铜板,走一步踢一下;母亲上班后,我会把新鞋翻出来穿上,到母亲帮我旧鞋换新鞋时,才发觉新鞋早已破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吹气进去会弹开发出呜呜声的小玩意儿,我很想得到,从母亲那儿偷了十个铜板,一股脑儿给了小贩,换了小玩意儿,回家后,给母亲按在床上狠打一顿。母亲不苟言笑,也不让小孩饶舌,我很少说话,尽管有时候会闹出笑话,比如说,家人说不能吃普通的牛肉,要吃清真的牛肉,我就提议大家吃清真的猪肉。
工厂有工屋,大部分被黑社会霸占。所有工屋一律是楼下客厅、厨房,楼上居室,每个月付4元租金。二叔有一间工屋。父亲常常不在家,母亲和我租住一个后楼,把三块床板放在两条长凳上。在板墙上贴花纸,不久,花纸上都是吸血白蚤,在床板上淋火水、烫沸水,还是被咬。上楼楼梯的近出口位置放了一块板当台用,上面放火水炉煮食,马桶放床旁边,行李塞在床下。整个工厂区有十多弄,名字很好听,有大旭里、梅芳里,我们住在樱华里第七弄,路中间有自来水和电供应。在炎热的夏天,我们爱把小板凳放在屋子外面的大街,坐着乘凉。二叔住在樱华里第二弄,跟我家隔一个马路;母亲打我的时候,我就跑出去,我跑得快,母亲追不到,祖母是我的护身符。二婶生的婴儿夭折了,让我去吃她的奶。我小时候身体羸弱,到十六岁乘船从辽宁去上海,连小孩半票都不用买。
大概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在北方辽宁(奉天)东塔兵工厂冷作间做工,赌博赢了很多钱,租用了杨宇霆第五姨太的物业,把全家连祖父母、叔祖父母、三叔父子俩、母亲和我,一起接到辽宁住。我读完小四,到北方辍学几年期间,父母亲带我在城里购物,我买了毛线和十字本,父亲工友的妻子教我编织毛线,我再对着本子学,给自己织了一条长毛线裤。接着,我在兵工厂小学继续念小四。
祖父闲着没事干,早上用拐杖点数外墙上的喇叭花,一天五次虔诚磕头做礼拜。我只跟从祖父在家里做过几次礼拜。一方面,我痛恨母亲和婶婶们在家里地位卑微,挨打挨駡;另一方面,我不相信鬼神,所以我后来叛离回教。到我参加托派组织后,同志们作弄我,在饭里放猪油,看不出来但我觉得有一股臭味。后来,少吃猪肉不是宗教原因,只是贫困。
在辽宁的时候,我听家里人说,二叔功夫很厉害。祖父懂功夫,我父亲头额上有一个硬包,用头额撞人,可以撞死人。父亲不肖,祖父再没有教他功夫,传了给二叔,二叔收了两百多徒弟;但在1927年出家后门准备回工厂的时候,被三个共产党人围着,他们打不过二叔,开枪杀死了他;工人恨他这个工头。在东北的时候,我听到父亲跟工友聊天,是否吹牛就不得而知了,他说,他在上海跟人打架,打死了人,被通缉,逃到新疆,做过官,再到法国,因为非法入境,被抓到牢狱里。牢狱的小房间有一个小窗对着街,他请一个路过的中国工人帮他弄到一把斧头,打了洞逃狱,但被抓回去,关进同一个牢房,之前打洞补上的墙还没干透,他有点功夫,用手肘把洞打穿,成功逃脱。四叔是律师楼的师爷,吊儿郎当,有一子一女,但他另外租房子跟别的女人同居。叔祖母是傻婆,螃蟹生吃,回上海后生一子,有一次带儿子看病拿了药,把药给儿子一次性全吞下,儿子死了。
我十四岁的时候,母亲生病,肚子很大,姨母在湖北汉口,母亲带我跟着她去治病,在仁济医院,同一天三个人做手术,另外两个人都死了,幸好她没死,从肚子里拿出来的血肉瘤,有13磅重,可能是没成胎儿的双胞死婴,应该是跟我父亲的梅毒有关。之后母亲再回辽宁。那时候,母亲住在医院,我很不懂事,不懂得担心她,反而向她诉苦,说吃不惯姨母做的饭菜。如果母亲当时死了,我真是不堪设想。
我陪母亲离开辽宁去湖北的时候,第一天出门,第二天父亲就招妓进屋。我们回到家里,看到被褥都换了新的。我被遗传了父亲的梅毒,第一胎堕胎,第二胎小产;怀第三胎时,在广州,产前检查验出有梅毒,说200元包治好,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生活费,哪来200元?于是自己买了914药,请同志帮忙打针。针药要打进血管,不能打进肌肉。头两针没事,第三针打不好,将914打进肌肉,晚上全身发肿,送去广州的红十字会方便医院。生产是在伯多禄医院,全身溃烂,生出来的男婴,眉目清秀,像个女的。邻床的孕妇生了女婴,看上去却像个男的。我当时病重,丈夫喂我一口一口吃饭,婴儿却一周后饿死了,丈夫把他拿到山边挖一个洞埋了。
我十五岁的时候,父亲输了钱,欠了赌债。一天,他带着我出去找朋友,到一个地方,他让我坐在客厅,他和别人在后头谈话。接着到另一个地方,最后到了一个妓院。父亲在后楼说话,一个外号叫“老江湖”的工友在靠近楼梯口的床上抽大烟,跟我说,“你父亲输了很多钱,用什么还赌债?”我忽然醒悟,立即轻轻地跑下楼梯,在马路边跳上一部人力车,请他拉快车,带我去辽宁东塔二边门;到弄口,看到母亲还有其它人。母亲在哭,因为父亲威胁要杀她。过了一会儿,父亲回来,大家都不说话。这是我险些给父亲卖到青楼妓院的故事。
我们一家在辽宁住了大概6年,父亲欠债想办法偷走,祖父等亲戚也陆续离开。父亲回上海租了一个店铺,卖牛肉汤,然后委托工友安排我们母女俩坐船回上海。我十六岁回到上海,不再上学了,到纱厂做工。纱厂工资比较稳定,有津贴,有工人住房,但是空气环境不好,而且工人忙着跟机器转动,一点不能松懈,就像查理卓别麟的《摩登时代》一样的情景。我第一天上班是夜班,工头不派活给我,早上离厂的时候,他向我提亲。我第二天就不去上班了。我们在新大昌杂货店租用了一个灶披间,后来我在这个灶披间的墙里收藏违禁的托派组织刊物。隔壁住了一个织绸女工,跟一个老男人同居。杂货店老板姓贾,除了开杂货店和在市中心开旅馆,也放高利贷。他的母亲和妻子同情我们,介绍我去学织绸。
织绸厂剥削很严重。我到织绸厂学师,先送礼给两个介绍人,头一年全部帮师傅做,工资归师傅。做满一定量之后,学徒只能拿2成的工资,然后4成、6成、8成,等到几年满师,才能拿全工资。学师的厂多半是织锦,经是真丝,纬是人造丝。自己派到机器的时候,做的是计件工,织一码算一码。了机要换新经的时候,等一两天完全没有工资;机器出毛病断了一梭丝,要一根一根地驳上;检查织绸的人可能很苛刻,会做出处罚(他下班后也会经常在路上被工人打);甚至工友之间嫉妒,故意下班交接时在机器上做手脚。所以,织绸工资好像高于纱厂,但平均下来,工资不如纱厂工人收入稳定。我当学徒时,有一次把手伸进机器的时候,一个工友开机,我的右手肘被夹着,去了医院,放了很多药纱进去,幸好没夹断,否则就残废了。为此,我停工几个月,没有分文工资收入。右手肘上留下了一道疤痕。
我学满师后,做了几年织绸工。工资仅够勉强糊口。织绸厂的好处是空气流通,一人一部机,可以坐着,下午累的时候,可以趴着休息一会。因为是件工制,晚饭后会回去做到10点。我对机器有兴趣,师傅来维修机器的时候,我会在旁边看着偷师,拿螺钉扳钳(士巴拿)学着修理机器,也略懂修理电器电灯。
我本来在沪东做工,不在美亚等大厂,而是在开利织绸厂。开利有二十多部机器,一排五部,有四、五排,全厂有几十个工人,工厂规模不算小,有职员宿舍。1937年8.13事变,日军打进上海,我和父母亲被迫从沪东逃难到比较安全的沪西英法租界区,后来东搬西搬,还是回到开利织绸厂。我也曾经在工厂做大机,不做花机,织航空飞机用的太空伞,有2码宽,用的是真丝,纬是湿的,织出来的航空布,不能有一丝跳线,要密密的不透水不透风。

我们上海织绸女工,上班穿裁缝做的旗袍,前后长短不同,前面长及脚背,后面长及鞋跟,旗袍叉开到大腿,方便活动。我不喜欢花布,旗袍大都是素色的。做学徒时,有一个男工是国民党党员,对我说“三从四德,妇女道也”,我装作没听见。经常有工友留字条向我表达爱意,我很严肃,不理睬他们。我身体不好,经常病,工头介绍一位驻厂中医师给我治病,他叫顾正洪,比我小两岁。他到我家给我治病,看到我小学的中英文读本,还有我做工后自己买来读的《古文观止》和诗词书。他追求我,向我父亲提亲;父亲说不能把我嫁给汉教。为了要与我结婚,他赶紧洗礼,改信回教,取得我家人的欢心。我和他订了婚。订婚时,他买糖果送给我们的亲戚族人,还做了两个大本的订婚书,一人一本,每次来看我,他都会带上他那本订婚书,以表明我们的关系,免生误会。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和姐姐弟弟,只听说过他弟弟在背后批评他哥哥过分顺我意。
一年多之后,我听顾正洪说他父亲是汉奸,我想,我不能做汉奸的儿媳妇,立即提出要解除婚约。为了躲避他,我不断搬家,换工厂,持续了几年。无论我搬到哪儿,他都能找到我,后来我知道父亲是内奸,给他通风报讯。他以羊肉酒菜讨好我父亲,父亲后来胃溃疡,说不定与此有关,但他肯定不是有意害我父亲。他又高又帅,皮肤白皙,善良、斯文、坦率,我觉得他是真心爱我,无奈他父亲是汉奸。有一次,我父亲把刀横在我脖子上,要逼我和顾正洪结婚。我说,我死也不要跟汉奸的儿子结婚。父亲将刀横在我脖子上威胁我,我把颈脖伸直,让他砍,吓得母亲向他下跪哭求,说,女儿给你杀了,你也没有女婿了,他才作罢,放下手上的刀。父亲后来因胃溃疡去世,母亲哭得很伤心,我一滴眼泪也没流。父亲去世后,母亲安排了一个伯父与顾正洪中午来我家,伯父要他同意解除婚约,挥拳打他胸口,顾正洪实时答应。之后,母亲把他送给我的一件我从没穿过的名贵灰背旗袍(长袖旗袍的夹里是灰鼠的黑背毛)退回给他。顾正洪家颇有社会地位,正式解除婚约时,报纸刊登了消息,标题是:“青年医生顾正洪婚变,未婚妻毅然决然提出离婚。”
1937年发生上海8.13事变时,我在沪东的开利织绸厂上班,已经是熟练工人了。8月13日那天早上,父亲一大清早出去了。我睡在床上,日本轰炸机投下炸弹,把我床边的窗玻璃震碎,碎片洒到我床上。我和母亲立即跑到楼下躲在楼梯底。没有父亲的讯息,我们匆忙用两张床单包裹细软,一人背一个包,没有从外白渡桥走,因为逃难的人拥挤堵塞在那。我们边走边看到轰炸机呜呜地飞过来,投下两颗炸弹,像生下两只蛋一样,接着是嘭嘭两声巨响。看到飞机时,我们找地方躲避,没有飞机时,我们赶快走,边走边躲边哭,从沪东经过浦东到海对面的沪西小沙渡工人区找同乡,到达时,父亲已经从外白渡桥来到这里。沪西是英法租界区,又是日本纱厂区,日本军不会轰炸这里。不久之后,我找到工作。可是,后来为了避开顾正洪,我不断搬家,重回沪东,回到开利织绸厂。

1939年,我参加了托派组织。少数派以郑超麟、王凡西、楼子春为首,主张对抗日采取失败主义。多数派以彭述之为首,主张抗日。从此,中国托派分成两个派别。固然,除非组织独裁,否则有不同意见,就会分裂。我参加后不久,听同志说,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给斯大林的特务谋杀了。
我参加组织,是在开利织绸厂的时候。那时已经解除婚约。开利在杨树浦,老板是中国人,抗日时趁机发国难财。我和母亲在亭子间住了一段时间。工人要排队领米,要求不要工资,只要每天一顿午饭,老板也不答应。当时米价是一元一斗米。在三八妇女节,上海的女工会自己放假,参加大规模游行。我很积极,在大路上倒着走,在地上写上标语:“八小时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一个共产党的男工调侃我:“这还不够激烈啊!”工友美玲与我一起斗争,她的丈夫蒋某是托派,女儿已10岁。蒋某像知识分子,身穿巴黎长衫,带流氓气,是织绸厂支部的负责人,五人支部除了蒋某和我,还有织绸厂三个男工,两人未婚,一人已婚。我讨厌他们开会时争风呷醋,抢着向我献殷勤。我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我参加组织后,自觉地、天真地搞罢工,常常单人匹马,在工厂筹备罢工,要求改善工人待遇。罢工时,要面对的有厂家的亲戚,有走狗,有共产党,也有托派。
蒋某对我有野心。我参加组织后没多久,有一次发热、腰疼,不能上班,卧病在床,美玲来看我,告诉我他丈夫的话,说我“年轻貌美,又勇敢,若有这样的女子抱在怀里,多么窝心”,又说他丈夫说我在某时某地接受了资方金钱,出卖工人。我听到后,不管生病卧床,立即起来跑到蒋家楼下,破口大駡他,说斯大林莫须有污蔑人,你和斯大林一样,造谣中伤。蒋某从楼上扔东西下来欲打伤我,我还是大骂。然后我回到家里对着母亲,边哭边诉苦。
当时我们住在汤丸店后面的灶披间,时间已经很晚了。就在那时候,一个日本兵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枪,我看到很危险,一个箭步从他腋下钻出去,在汤丸店里装作是老板娘招呼客人。日本兵悻悻然离开,店东立即上了排门,楼上楼下全熄灯,前楼住户让我躲在前楼床上假装前楼住客的孩子。没多久,楼下有人大力敲门,我们不吭声。一到天亮,母亲和我立即逃到沪西,同时我也离开了组织。听说蒋某后来死于中共狱中。
我继续在织绸厂搞罢工,组织对我观察了一段时期,认为我可信任,又把我找回去。我下班后,会联络较为要好的工人谈话。我认识了罗子玲,她哥哥是小织绸厂经理,我影响了罗子玲参加组织,甚至在他哥哥的织绸厂和她一起搞罢工。我做过很多织绸厂,有时候是长夜班,一周上日班,一周上夜班,每班12小时。当我在沪西做一个有几十个工人的大厂时,我写信代表工人,要资方改善待遇,接着罢工;几天后,我怀疑被中国共产党出卖,我和罗子玲及几名工友被资方抓进巡捕房。我的30岁生日,在牢狱中度过。我记得四叔送来一碗红焖羊肉面,庆祝我生日。
有一个叫阿杨的女同志,年纪较轻,广东人,戴眼镜,学生出身,香港的体育健将,从香港来上海,沉默寡言,比较呆板。我们感情很好,她很疼我,常带我游玩。我在织绸厂上班时,她跟我在新大昌杂货店的灶披间一起住,母亲煮了饭,她把饭菜送来工厂给我吃,路程挺远的。我们入狱后,她认为其它同志不关心我们被捕,尽管王国龙劝她不要探监,她坚持要来送饭,结果也被捕。被问讯的时候,警察骗她别人都说了,她太天真,没经验,供出了其它同志的名字和住处。她被送进我们的囚室时,只说“我不说你们都说了!”我很气愤,拉她咬她的鼻子,骂她出卖了同志。鼻子滑,我咬不住。她很快就被释放了。同志说出狱后,阿杨疯了,有人看到她一丝不挂拾街上的食物,喝沟渠里的水。
狱中,五个人一个牢房,除了我和阿杨外,还有同志罗丽萍,同情者尹静文;先我们入狱的,还有一个吸毒的女犯,毒瘾发作的时候大叫大喊。牢房约10平方米,没有床,没有水,只有一个坐厕。我接厕所的水来洗脸,没有换洗的衣服。食物是一股臭味的玉米连渣搅在一起,和一条不咸的雪里红咸菜。开始我们都不吃,后来饿了,警察把面包扔进来,把我们当作是狗,我们也没法,只能捡来吃了。
这次同时被捕的有三个男同志高擎宇、李永爵、刘康,在隔壁的囚房里。在日本宪兵的指挥下,李、刘饱受酷刑逼供,要供出彭述之等同志的地址,但是他们坚持不说,连施行酷刑的中国警察也称他们为硬汉子。高擎宇是老师,很斯文,警察没对他逼供。
警察也没有向我问口供,有一个警察还逗我玩,把两只手放在头角上,让我猜他姓什么,我说“杨”,他说嘻嘻猜对了。狱中度过多久我也不清楚,大概几个月吧。狱中有一个高级日本军官喜欢我,出狱时他要约见我,我故意打扮得很丑,不搭理他,他也作罢。有工友为我可惜,说丢了做官太太的大好机会。我不屑一顾。
出狱后,由于我到处组织工人争取权益的名声太大了,没有哪个织绸厂愿意聘请我,我早上上班,中午吃饭回来,老板已经不准我进厂了,半天的工资也拿不到。日本投降后,我还是怎样都找不到工作。我不到十岁的时候,到姨父乡下玩,学会打算盘,于是我在家自修珠算、会计。接着叔父介绍我到一间工厂做簿记,不久被老板转到虞尔雅清路的一品香旅馆的中菜部,做正式会计。我要做两本账,真假各一,国民党的官员来查账,被查的是假账,票据齐全,一点漏洞都没有被查出。
1948年,我在广州患病时,在报纸上看到广州税务局招聘会计的广告,我应聘被录取,在税务局做了几个月会计。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是我认为自己没有走错路。在这自私自利的黑暗社会里,我受尽折磨,委曲求全。我奋斗一生的理想,是要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国界之分,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劳动者是主人,人人平等自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剥削,没有人祸,避开天灾,最后进入共产主义,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
我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