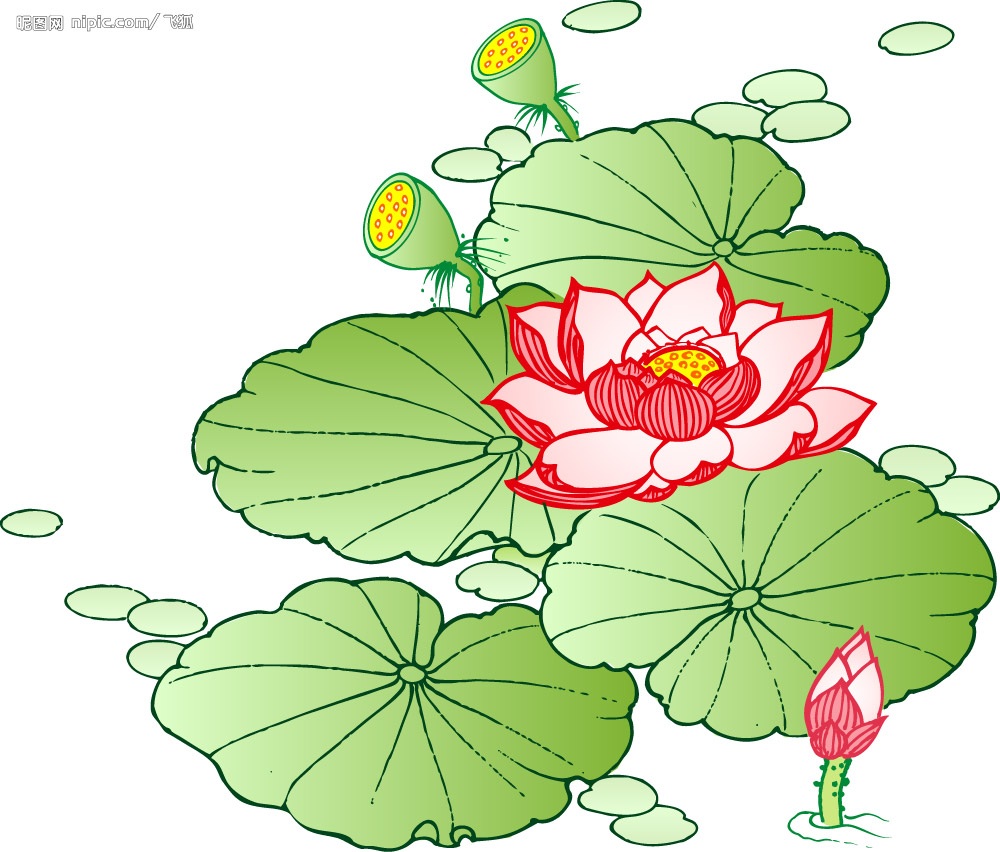我無悔!
魏幗英
我的祖父原來在湖北務農,娶妻後移居上海做小販,賣湯丸,住在小沙渡的工人區。街上很多店鋪是回教徒開的,招牌上有“清真”的字樣。祖父在小沙渡工人區協助籌款創辦清真寺,牲口要經他宰殺,別人稱他為爸爸,意即教父。祖父生四子,我父親是長子,我是獨孩,也是五代唯一的女孩。
外祖父在農村給人家“磅牛”,拍拍牛身就能估量牛有多重,殺牛後切開來稱,很準確。外祖父重男輕女,有2子2女。大舅舅幫人以馬代步,是被馬踢死的。小舅舅務農。
我母親三歲時,外祖母死了,母親哭壞了眼睛,靠比她大七歲的姐姐照顧。外祖父後來娶了填房。母親想嫁給城裏人,把眼睛醫治好,嫁了比她大兩歲的我的父親,24歲時生我。父親嫖賭飲吹,染上性病。二叔在監獄做事,把麵包屑拿回家,母親懷著我時,只吃麵包屑,身體很差。祖母是出名的刻薄惡婆,經常打四個兒媳婦,母親是她的同鄉,少點挨打挨駡。據說,祖母很凶,三個小夥子都打不過她。她打罵兒媳婦後,還不讓吃飯,兒媳婦之間會偷偷送飯。母親生倒睫毛,用夾子夾著眼皮,祖母打她的時候,偏打她眼睛。我出生後,幾個月打噎;祖母還好意思說,寶寶打噎,是因為在娘胎裏受了氣。
我是五代唯一的女孩,出生的時候,小鵝蛋臉,很美,阿訇為我洗禮時,祝賀我祖父,說你添了個天使。
我六歲的時候,祖母提出要把我送到日本紗廠筒子間做細紗童工,母親不答應。當時,二叔是崇信紗廠的職員,在廠裏有點權力,所以祖母在工廠負責派廁紙;母親同另一人負責在打好包的紗包上蓋章,活輕,下午三、四點可以下班回家。如果我做紗廠的養成工,會有工資。
母親讓我報讀崇信紗廠的附屬崇信小學,讀到小四。我們家窮,有一個同班同學叫姚桂香,與我很要好,她和妹妹上學由家裏的私人黃包車接送,路經工人房區把我接上。我讀書時比較懵,小一的課文“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白布五匹六匹”,“燕子爾又來乎,舊巢破,不可居。燕子銜泥銜草,重造新巢”,我都琅琅上口,可是一本書讀下來,我還搞不清“人”字原來在第一頁。小三的時候開始讀英文,老師問“時鐘”怎麼說,我答不上,後來能答是“clock”,老師問怎麼拼寫,我不知道,老師給我板尺,自己打手板。有一次,我問母親拿一個銅板買英文練習本,母親不識字,要我唸英文給她聽,我大聲把26個英文字母唸了一遍,母親還以為我英文流利,給我銅板買練習本去。
我讀書不大行,但是好奇心重,觀察力強。母親比較迷信,曾經請拖著駱駝的相士給我算命。我不迷信,自己一個人在街上觀察擺地攤的相士怎樣用雀鳥占卜,雀鳥會啄出客人的生肖紙片,很準確,但是我拆穿相士說,你不要指手畫腳,要讓雀鳥自己找。我對機器很感興趣。大概八歲的時候,有一次偷拿了叔叔的掛表,拆開來看為什麼能轉動,接著沒法拼好,趕快把零件扔到小巷對面的樓房裏,二房東知道,幸好沒告訴母親。十來歲在北方的時候,我又拆開了一個座台鐘,然後重新裝嵌,分針慢了15分鐘,我勉強把針撥過去,沒被人發現。
母親有很強的自尊,教導我要有骨氣,不貪婪,不依賴。我自小走路只往前走,目不斜視。也很執著,兩條小辮子不對稱,一定要重紮,否則不肯出門。母親管教很嚴厲,知道我不規矩會教訓我。沒有玩具,我用繩子綁著一塊銅板,走一步踢一下;母親上班後,我會把新鞋翻出來穿上,到母親幫我舊鞋換新鞋時,才發覺新鞋早已破爛。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吹氣進去會彈開發出嗚嗚聲的小玩意兒,我很想得到,從母親那兒偷了十個銅板,一股腦兒給了小販,換了小玩意兒,回家後,給母親按在床上狠打一頓。母親不苟言笑,也不讓小孩饒舌,我很少說話,儘管有時候會鬧出笑話,比如說,家人說不能吃普通的牛肉,要吃清真的牛肉,我就提議大家吃清真的豬肉。
工廠有工屋,大部分被黑社會霸佔。所有工屋一律是樓下客廳、廚房,樓上居室,每個月付4元租金。二叔有一間工屋。父親常常不在家,母親和我租住一個後樓,把三塊床板放在兩條長凳上。在板牆上貼花紙,不久,花紙上都是吸血白蚤,在床板上淋火水、燙沸水,還是被咬。上樓樓梯的近出口位置放了一塊板當台用,上面放火水爐煮食,馬桶放床旁邊,行李塞在床下。整個工廠區有十多弄,名字很好聽,有大旭裏、梅芳裏,我們住在櫻華裏第七弄,路中間有自來水和電供應。在炎熱的夏天,我們愛把小板凳放在屋子外面的大街,坐著乘涼。二叔住在櫻華裏第二弄,跟我家隔一個馬路;母親打我的時候,我就跑出去,我跑得快,母親追不到,祖母是我的護身符。二嬸生的嬰兒夭折了,讓我去吃她的奶。我小時候身體羸弱,到十六歲乘船從遼寧去上海,連小孩半票都不用買。
大概十一歲的時候,父親在北方遼寧(奉天)東塔兵工廠冷作間做工,賭博贏了很多錢,租用了楊宇霆第五姨太的物業,把全家連祖父母、叔祖父母、三叔父子倆、母親和我,一起接到遼寧住。我讀完小四,到北方輟學幾年期間,父母親帶我在城裏購物,我買了毛線和十字本,父親工友的妻子教我編織毛線,我再對著本子學,給自己織了一條長毛線褲。接著,我在兵工廠小學繼續唸小四。
祖父閑著沒事幹,早上用拐杖點數外牆上的喇叭花,一天五次虔誠磕頭做禮拜。我只跟從祖父在家裏做過幾次禮拜。一方面,我痛恨母親和嬸嬸們在家裏地位卑微,挨打挨駡;另一方面,我不相信鬼神,所以我後來叛離回教。到我參加托派組織後,同志們作弄我,在飯裏放豬油,看不出來但我覺得有一股臭味。後來,少吃豬肉不是宗教原因,只是貧困。
在遼寧的時候,我聽家裏人說,二叔功夫很厲害。祖父懂功夫,我父親頭額上有一個硬包,用頭額撞人,可以撞死人。父親不肖,祖父再沒有教他功夫,傳了給二叔,二叔收了兩百多徒弟;但在1927年出家後門準備回工廠的時候,被三個共產黨人圍著,他們打不過二叔,開槍殺死了他;工人恨他這個工頭。在東北的時候,我聽到父親跟工友聊天,是否吹牛就不得而知了,他說,他在上海跟人打架,打死了人,被通緝,逃到新疆,做過官,再到法國,因為非法入境,被抓到牢獄裏。牢獄的小房間有一個小窗對著街,他請一個路過的中國工人幫他弄到一把斧頭,打了洞逃獄,但被抓回去,關進同一個牢房,之前打洞補上的牆還沒乾透,他有點功夫,用手肘把洞打穿,成功逃脫。四叔是律師樓的師爺,吊兒郎當,有一子一女,但他另外租房子跟別的女人同居。叔祖母是傻婆,螃蟹生吃,回上海後生一子,有一次帶兒子看病拿了藥,把藥給兒子一次性全吞下,兒子死了。
我十四歲的時候,母親生病,肚子很大,姨母在湖北漢口,母親帶我跟著她去治病,在仁濟醫院,同一天三個人做手術,另外兩個人都死了,幸好她沒死,從肚子裏拿出來的血肉瘤,有13磅重,可能是沒成胎兒的雙胞死嬰,應該是跟我父親的梅毒有關。之後母親再回遼寧。那時候,母親住在醫院,我很不懂事,不懂得擔心她,反而向她訴苦,說吃不慣姨母做的飯菜。如果母親當時死了,我真是不堪設想。
我陪母親離開遼寧去湖北的時候,第一天出門,第二天父親就招妓進屋。我們回到家裏,看到被褥都換了新的。我被遺傳了父親的梅毒,第一胎墮胎,第二胎小產;懷第三胎時,在廣州,產前檢查驗出有梅毒,說200元包治好,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生活費,哪來200元?於是自己買了914藥,請同志幫忙打針。針藥要打進血管,不能打進肌肉。頭兩針沒事,第三針打不好,將914打進肌肉,晚上全身發腫,送去廣州的紅十字會方便醫院。生產是在伯多祿醫院,全身潰爛,生出來的男嬰,眉目清秀,像個女的。鄰床的孕婦生了女嬰,看上去卻像個男的。我當時病重,丈夫喂我一口一口吃飯,嬰兒卻一周後餓死了,丈夫把他拿到山邊挖一個洞埋了。
我十五歲的時候,父親輸了錢,欠了賭債。一天,他帶著我出去找朋友,到一個地方,他讓我坐在客廳,他和別人在後頭談話。接著到另一個地方,最後到了一個妓院。父親在後樓說話,一個外號叫“老江湖”的工友在靠近樓梯口的床上抽大煙,跟我說,“你父親輸了很多錢,用什麼還賭債?”我忽然醒悟,立即輕輕地跑下樓梯,在馬路邊跳上一部人力車,請他拉快車,帶我去遼寧東塔二邊門;到弄口,看到母親還有其他人。母親在哭,因為父親威脅要殺她。過了一會兒,父親回來,大家都不說話。這是我險些給父親賣到青樓妓院的故事。
我們一家在遼寧住了大概6年,父親欠債想辦法偷走,祖父等親戚也陸續離開。父親回上海租了一個店鋪,賣牛肉湯,然後委託工友安排我們母女倆坐船回上海。我十六歲回到上海,不再上學了,到紗廠做工。紗廠工資比較穩定,有津貼,有工人住房,但是空氣環境不好,而且工人忙著跟機器轉動,一點不能鬆懈,就像查理卓別林的《摩登時代》一樣的情景。我第一天上班是夜班,工頭不派活給我,早上離廠的時候,他向我提親。我第二天就不去上班了。我們在新大昌雜貨店租用了一個灶披間,後來我在這個灶披間的牆裏收藏違禁的托派組織刊物。隔壁住了一個織綢女工,跟一個老男人同居。雜貨店老闆姓賈,除了開雜貨店和在市中心開旅館,也放高利貸。他的母親和妻子同情我們,介紹我去學織綢。
織綢廠剝削很嚴重。我到織綢廠學師,先送禮給兩個介紹人,頭一年全部幫師傅做,工資歸師傅。做滿一定量之後,學徒只能拿2成的工資,然後4成、6成、8成,等到幾年滿師,才能拿全工資。學師的廠多半是織錦,經是真絲,緯是人造絲。自己派到機器的時候,做的是計件工,織一碼算一碼。了機要換新經的時候,等一兩天完全沒有工資;機器出毛病斷了一梭絲,要一根一根地駁上;檢查織綢的人可能很苛刻,會做出處罰(他下班後也會經常在路上被工人打);甚至工友之間嫉妒,故意下班交接時在機器上做手腳。所以,織綢工資好像高於紗廠,但平均下來,工資不如紗廠工人收入穩定。我當學徒時,有一次把手伸進機器的時候,一個工友開機,我的右手肘被夾著,去了醫院,放了很多藥紗進去,幸好沒夾斷,否則就殘廢了。為此,我停工幾個月,沒有分文工資收入。右手肘上留下了一道疤痕。
我學滿師後,做了幾年織綢工。工資僅夠勉強糊口。織綢廠的好處是空氣流通,一人一部機,可以坐著,下午累的時候,可以趴著休息一會。因為是件工制,晚飯後會回去做到10點。我對機器有興趣,師傅來維修機器的時候,我會在旁邊看著偷師,拿螺釘扳鉗(士巴拿)學著修理機器,也略懂修理電器電燈。
我本來在滬東做工,不在美亞等大廠,而是在開利織綢廠。開利有二十多部機器,一排五部,有四、五排,全廠有幾十個工人,工廠規模不算小,有職員宿舍。1937年8.13事變,日軍打進上海,我和父母親被迫從滬東逃難到比較安全的滬西英法租界區,後來東搬西搬,還是回到開利織綢廠。我也曾經在工廠做大機,不做花機,織航空飛機用的太空傘,有2碼寬,用的是真絲,緯是濕的,織出來的航空布,不能有一絲跳線,要密密的不透水不透風。

我們上海織綢女工,上班穿裁縫做的旗袍,前後長短不同,前面長及腳背,後面長及鞋跟,旗袍叉開到大腿,方便活動。我不喜歡花布,旗袍大都是素色的。做學徒時,有一個男工是國民黨黨員,對我說“三從四德,婦女道也”,我裝作沒聽見。經常有工友留字條向我表達愛意,我很嚴肅,不理睬他們。我身體不好,經常病,工頭介紹一位駐廠中醫師給我治病,他叫顧正洪,比我小兩歲。他到我家給我治病,看到我小學的中英文讀本,還有我做工後自己買來讀的《古文觀止》和詩詞書。他追求我,向我父親提親;父親說不能把我嫁給漢教。為了要與我結婚,他趕緊洗禮,改信回教,取得我家人的歡心。我和他訂了婚。訂婚時,他買糖果送給我們的親戚族人,還做了兩個大本的訂婚書,一人一本,每次來看我,他都會帶上他那本訂婚書,以表明我們的關係,免生誤會。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父母和姐姐弟弟,只聽說過他弟弟在背後批評他哥哥過分順我意。
一年多之後,我聽顧正洪說他父親是漢奸,我想,我不能做漢奸的兒媳婦,立即提出要解除婚約。為了躲避他,我不斷搬家,換工廠,持續了幾年。無論我搬到哪兒,他都能找到我,後來我知道父親是內奸,給他通風報訊。他以羊肉酒菜討好我父親,父親後來胃潰瘍,說不定與此有關,但他肯定不是有意害我父親。他又高又帥,皮膚白皙,善良、斯文、坦率,我覺得他是真心愛我,無奈他父親是漢奸。有一次,我父親把刀橫在我脖子上,要逼我和顧正洪結婚。我說,我死也不要跟漢奸的兒子結婚。父親將刀橫在我脖子上威脅我,我把頸脖伸直,讓他砍,嚇得母親向他下跪哭求,說,女兒給你殺了,你也沒有女婿了,他才作罷,放下手上的刀。父親後來因胃潰瘍去世,母親哭得很傷心,我一滴眼淚也沒流。父親去世後,母親安排了一個伯父與顧正洪中午來我家,伯父要他同意解除婚約,揮拳打他胸口,顧正洪即時答應。之後,母親把他送給我的一件我從沒穿過的名貴灰背旗袍(長袖旗袍的夾裏是灰鼠的黑背毛)退回給他。顧正洪家頗有社會地位,正式解除婚約時,報紙刊登了消息,標題是:“青年醫生顧正洪婚變,未婚妻毅然決然提出離婚。”
1937年發生上海8.13事變時,我在滬東的開利織綢廠上班,已經是熟練工人了。8月13日那天早上,父親一大清早出去了。我睡在床上,日本轟炸機投下炸彈,把我床邊的窗玻璃震碎,碎片灑到我床上。我和母親立即跑到樓下躲在樓梯底。沒有父親的訊息,我們匆忙用兩張床單包裹細軟,一人背一個包,沒有從外白渡橋走,因為逃難的人擁擠堵塞在那。我們邊走邊看到轟炸機嗚嗚地飛過來,投下兩顆炸彈,像生下兩隻蛋一樣,接著是嘭嘭兩聲巨響。看到飛機時,我們找地方躲避,沒有飛機時,我們趕快走,邊走邊躲邊哭,從滬東經過浦東到海對面的滬西小沙渡工人區找同鄉,到達時,父親已經從外白渡橋來到這裏。滬西是英法租界區,又是日本紗廠區,日本軍不會轟炸這裏。不久之後,我找到工作。可是,後來為了避開顧正洪,我不斷搬家,重回滬東,回到開利織綢廠。

1939年,我參加了托派組織。少數派以鄭超麟、王凡西、樓子春為首,主張對抗日採取失敗主義。多數派以彭述之為首,主張抗日。從此,中國托派分成兩個派別。固然,除非組織獨裁,否則有不同意見,就會分裂。我參加後不久,聽同志說,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給斯大林的特務謀殺了。
我參加組織,是在開利織綢廠的時候。那時已經解除婚約。開利在楊樹浦,老闆是中國人,抗日時趁機發國難財。我和母親在亭子間住了一段時間。工人要排隊領米,要求不要工資,只要每天一頓午飯,老闆也不答應。當時米價是一元一斗米。在三八婦女節,上海的女工會自己放假,參加大規模遊行。我很積極,在大路上倒著走,在地上寫上標語:“八小時工作,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一個共產黨的男工調侃我:“這還不夠激烈啊!”工友美玲與我一起鬥爭,她的丈夫蔣某是托派,女兒已10歲。蔣某像知識份子,身穿巴黎長衫,帶流氓氣,是織綢廠支部的負責人,五人支部除了蔣某和我,還有織綢廠三個男工,兩人未婚,一人已婚。我討厭他們開會時爭風呷醋,搶著向我獻殷勤。我一本正經,不苟言笑。我參加組織後,自覺地、天真地搞罷工,常常單人匹馬,在工廠籌備罷工,要求改善工人待遇。罷工時,要面對的有廠家的親戚,有走狗,有共產黨,也有托派。
蔣某對我有野心。我參加組織後沒多久,有一次發熱、腰疼,不能上班,臥病在床,美玲來看我,告訴我他丈夫的話,說我“年輕貌美,又勇敢,若有這樣的女子抱在懷裏,多麼窩心”,又說他丈夫說我在某時某地接受了資方金錢,出賣工人。我聽到後,不管生病臥床,立即起來跑到蔣家樓下,破口大駡他,說斯大林莫須有污蔑人,你和斯大林一樣,造謠中傷。蔣某從樓上扔東西下來欲打傷我,我還是大罵。然後我回到家裏對著母親,邊哭邊訴苦。
當時我們住在湯丸店後面的灶披間,時間已經很晚了。就在那時候,一個日本兵推門進來,手裏拿著槍,我看到很危險,一個箭步從他腋下鑽出去,在湯丸店裏裝作是老闆娘招呼客人。日本兵悻悻然離開,店東立即上了排門,樓上樓下全熄燈,前樓住戶讓我躲在前樓床上假裝前樓住客的孩子。沒多久,樓下有人大力敲門,我們不吭聲。一到天亮,母親和我立即逃到滬西,同時我也離開了組織。聽說蔣某後來死於中共獄中。
我繼續在織綢廠搞罷工,組織對我觀察了一段時期,認為我可信任,又把我找回去。我下班後,會聯絡較為要好的工人談話。我認識了羅子玲,她哥哥是小織綢廠經理,我影響了羅子玲參加組織,甚至在他哥哥的織綢廠和她一起搞罷工。我做過很多織綢廠,有時候是長夜班,一周上日班,一周上夜班,每班12小時。當我在滬西做一個有幾十個工人的大廠時,我寫信代表工人,要資方改善待遇,接著罷工;幾天後,我懷疑被中國共產黨出賣,我和羅子玲及幾名工友被資方抓進巡捕房。我的30歲生日,在牢獄中度過。我記得四叔送來一碗紅燜羊肉面,慶祝我生日。
有一個叫阿楊的女同志,年紀較輕,廣東人,戴眼鏡,學生出身,香港的體育健將,從香港來上海,沉默寡言,比較呆板。我們感情很好,她很疼我,常帶我遊玩。我在織綢廠上班時,她跟我在新大昌雜貨店的灶披間一起住,母親煮了飯,她把飯菜送來工廠給我吃,路程挺遠的。我們入獄後,她認為其他同志不關心我們被捕,儘管王國龍勸她不要探監,她堅持要來送飯,結果也被捕。被問訊的時候,警察騙她別人都說了,她太天真,沒經驗,供出了其他同志的名字和住處。她被送進我們的囚室時,只說“我不說你們都說了!”我很氣憤,拉她咬她的鼻子,罵她出賣了同志。鼻子滑,我咬不住。她很快就被釋放了。同志說出獄後,阿楊瘋了,有人看到她一絲不掛拾街上的食物,喝溝渠裏的水。
獄中,五個人一個牢房,除了我和阿楊外,還有同志羅麗萍,同情者尹靜文;先我們入獄的,還有一個吸毒的女犯,毒癮發作的時候大叫大喊。牢房約10平方米,沒有床,沒有水,只有一個坐廁。我接廁所的水來洗臉,沒有換洗的衣服。食物是一股臭味的玉米連渣攪在一起,和一條不鹹的雪裏紅鹹菜。開始我們都不吃,後來餓了,警察把麵包扔進來,把我們當作是狗,我們也沒法,只能撿來吃了。
這次同時被捕的有三個男同志高擎宇、李永爵、劉康,在隔壁的囚房裏。在日本憲兵的指揮下,李、劉飽受酷刑逼供,要供出彭述之等同志的地址,但是他們堅持不說,連施行酷刑的中國警察也稱他們為硬漢子。高擎宇是老師,很斯文,警察沒對他逼供。
警察也沒有向我問口供,有一個警察還逗我玩,把兩隻手放在頭角上,讓我猜他姓什麼,我說“楊”,他說嘻嘻猜對了。獄中度過多久我也不清楚,大概幾個月吧。獄中有一個高級日本軍官喜歡我,出獄時他要約見我,我故意打扮得很醜,不搭理他,他也作罷。有工友為我可惜,說丟了做官太太的大好機會。我不屑一顧。
出獄後,由於我到處組織工人爭取權益的名聲太大了,沒有哪個織綢廠願意聘請我,我早上上班,中午吃飯回來,老闆已經不准我進廠了,半天的工資也拿不到。日本投降後,我還是怎樣都找不到工作。我不到十歲的時候,到姨父鄉下玩,學會打算盤,於是我在家自修珠算、會計。接著叔父介紹我到一間工廠做簿記,不久被老闆轉到虞爾雅清路的一品香旅館的中菜部,做正式會計。我要做兩本賬,真假各一,國民黨的官員來查賬,被查的是假賬,票據齊全,一點漏洞都沒有被查出。
1948年,我在廣州患病時,在報紙上看到廣州稅務局招聘會計的廣告,我應聘被錄取,在稅務局做了幾個月會計。
也許有人會認為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可是我認為自己沒有走錯路。在這自私自利的黑暗社會裏,我受盡折磨,委曲求全。我奮鬥一生的理想,是要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沒有國界之分,沒有貧富之分,只有勞動者是主人,人人平等自由,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沒有剝削,沒有人禍,避開天災,最後進入共產主義,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
我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