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動計劃”—— 致比利時共產黨員-國際主義者
(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支部 (1934)
列.托洛茨基

親愛的同志們:
毋須對你們說,我在最近幾天內十分認真地研究了你們寄來的報紙、雜誌、記錄、信件等。由於材料的出色的選擇,我有可能在相對短的期限內瞭解整體問題,和在你們的組織中產生的分歧的實質。你們的爭論的嚴格的原則性未受個人激化的影響,使人對你們的組織的整體精神,和它的道德-政治水準產生最有利的概念。我只能表達熱烈的願望,讓這個精神不僅在比利時支部中得到保持和鞏固,還能成為在我們所有支部(無一例外)中的主導精神。
我想在下面就有爭議的問題的實質表達的那些看法,既不覬覦全面,也不覬覦完整。我已遠離行動舞臺。這樣重要的因素如群眾情緒,是不能僅憑報紙和文件就對自己說清楚的:需要摸工人會議的脈搏,我是做不到的。但由於事關的是蘇維埃的一般原則,旁觀者的情況也許還有某些優勢,因為有機會超越細節,集中到主要問題上。
現在轉入事情的實質。
首先,我看不到能夠迫使我們放棄“讓比利時工人奪取政權!”的口號的理由,我認為這是中心點。當我們第一次提出這個口號時,我們當然對比利時社會黨的性質有清楚的認識,它不想也不會鬥爭,它在幾十年的時間裡習慣了在無產階級的列車上扮演資產階級制動器的角色,它害怕聯合之外的政權,因為它為了不接受工人的要求的可能性,離不開資產階級盟友。
所有這些我們都知道。但我們還知道,不僅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還有它的議會國家機器也進入了嚴重危機的階段,它含有人民群眾情緒迅速(相對的)交替的可能性,還有議會和政府組合的迅速交替。如果注意到,在第三國際比利時支部的微不足道和革命一翼極端軟弱的情況下,比利時社會黨和改良主義的辛迪加在無產階級中占絕對的統治地位,就清楚了,整個政治局勢應該對無產階級暗示社會黨政府的思想。
我們預先認為,建立這樣的政府無疑是向前邁了一步。當然不在這個意義上,王德威爾得、德·曼[1]之流的政府能夠在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事業上扮演進步角色,而是在那個意義上,社會黨政府的經驗在這些條件下對發展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有十分進步的意義。這樣,社會黨政府的口號指望的不是某種極端的變動,而是相對較長的政治時期。如果社會黨在其當政之前就開始迅速削弱,把自己的影響讓位於革命黨,我們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放棄這個口號;哎,但是今天,這樣的前景是純理論上的。無論是整體政治形勢,還是在無產階級內部的力量對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為放棄社會黨政權的口號辯解!
無論如何都不是被華麗地稱為“勞動計劃”(更確切地應稱為欺騙勞動者的計劃)的德·曼的計劃,能夠讓我們放棄這個時期的核心政治口號。“勞動計劃”應該是資產階級民主(或哪怕是半民主)保守主義的新的(或翻新的)工具。但全部實質是形勢極端尖銳,威脅社會黨本身存在的危險的極度迫近,迫使它違背自己的意志抓住雙刃武器,從民主保守主義的角度來看,這是十分冒險的。
資本主義的動態平衡已經永遠失去了。議會制度的平衡也傷痕累累,正在坍塌。最後,改良主義的保守的平衡——這是同一個鏈條中的一環——也開始動搖,後者為了拯救資產階級制度而被迫公然放棄它。這樣的形勢在自身中蘊涵著巨大的革命機會(與危險並存)。我們不應該放棄社會黨政權的口號,而是相反,賦予這個口號盡可能大的戰鬥性質和尖銳性。
在我們之中無須說,為這個口號進行的鼓動中不應該有絲毫的虛假和做作、緩和矛盾、外交手腕、虛假的或程式化的信任。我們讓左派社會黨黨員往事業中放奶油和蜜(以斯派克[2]的精神)。而我們還像以往一樣使用醋和辣椒。
在寄給我的材料中看到了這種看法,工人群眾對待“勞動計劃”十分冷漠,他們處在壓抑階段,在這些條件下“社會黨政權”的口號只能讓人產生幻想,然後導致失望。在這裡沒有可能為自己對比利時無產階級各階層、集團的情緒得出明確的概念,但我認為工人一定的精神上的疲倦和消極的可能性是完全可能的。但首先,這個情緒的本身不是最終的,毋寧說它具有的是期待性,而不是絕望的。當然,在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會認為,比利時無產階級在幾年內都不能進行鬥爭。痛苦、仇恨、咬牙切齒的情緒在他內心積聚了很多,它們尋求宣洩。為了免於死亡,社會黨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工人運動。為了讓工人變得好說話,它需要資產者的説明。它當然對運動會超越它怕得要命。在共產國際微不足道、革命集團軟弱的情況下,在新鮮的德國經驗的影響下,社會黨等待從右邊來的直接危險,而不是從大左邊。沒有這些前提,“社會黨政權”的口號根本就沒有任何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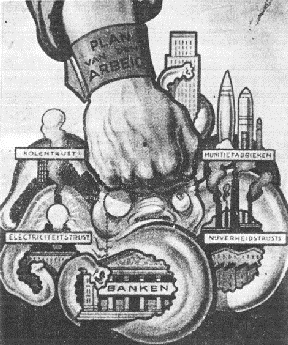
德·曼計劃和與它相關的社會黨的鼓動散佈幻想,並會引起失望,我們中的任何人對此都不會懷疑的。但社會黨、它在無產階級中的影響和它的計劃、它的儀式化的代表大會、它的宣傳鼓動是客觀事實:我們既不能排斥它們,也不能越過它們。我們的任務是雙重的:第一,對進步工人解釋“計劃”的政治意義,即破譯社會黨在所有階段上的手腕;第二,用事實對最廣大的工人表明,當資產階級企圖阻礙計劃實施時,我們與他們攜手鬥爭,幫助他們積累經驗。我們分擔鬥爭的全部困難,但不分享它的幻想。我們批評幻想,但不是鞏固工人的消極,不給它虛假的理論辯解,而是相反,推動工人前進。在這些條件下,對“勞動計劃”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將意味的不是消極性的加深,而是相反,工人轉上革命道路。
我想在近幾天為“計劃”本身專寫一篇文章。由於此信的極度匆忙的性質,我在此只
限於寥寥數語。首先,我認為把這個計劃與法西斯的經濟政策拉近是錯誤的。貸款、重工業和能源工業的一定部門的國有化本身沒有任何法西斯的東西。由於法西斯提出的(在得到政權之前!)國有化的口號是為了與“超資本主義”鬥爭的目的,它簡單地剽竊了社會主義綱領的現成說法。在德·曼的計劃中,我們看到——在社會黨的資產階級性質下的——被社會黨用來冒充社會主義的因素國家資本主義的綱領,但它能違背社會黨,變成真的社會主義的因素。
在經濟綱領本身的範圍內(“勞動計劃”),我以為我們應該把三點提到首要位置:
a)關於贖買。抽象地議論,社會主義革命不排除所有和任何形式的對資本家的私有財產的贖買。馬克思當初曾表達過這種意思,如果“能從這個匪幫那兒贖買”(從資本家那兒),是不錯的。在世界大戰前,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如果注意到民族和世界經濟體今天的瓦解,以及人民群眾的貧窮,贖買就是致命的操作,它應該在開始時為新制度造成完全承受不了的負擔。我們能夠也應該用手中的數字讓每個工人都明白這點。
b)與沒有贖買的剝奪一起,我們應該提出工人監督的口號。與德·曼(見《比利時的辛迪加運動》1933年第11期,第297頁)不同,國有化和工人監督根本不是相互排斥的。甚至如果政府是極左的,充滿了最好的意圖,我們也將支援工人對生產和流通的監督:我們不想要官僚對國有化的工業的管理,我們要求工人本身通過工廠委員會、工會等直接參加監督和管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經濟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框架中。
c)計劃對土地財產本身未置一詞。這裡必須有針對農業工人和貧農的口號。但對這個複雜的問題我力求專門談一下。
必須轉入計劃的政治方面。在此自然會提出兩個問題:a)為實現計劃的鬥爭方法(其中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以及b)對城鄉小資產階級的態度。
在其刊登在辛迪加的機關刊物上的綱領性的講話中,德·曼斷然否定了革命鬥爭(總罷工和起義)。是啊,能從這些人那兒期待別的東西嗎?不管主要旨在安慰左派傻瓜的那些個別的保留和糾正如何,黨的官方立場仍是議會克汀病的立場。我們的批評的主要打擊應該對準這條路線,不僅反對整個黨,還要反對它的左翼(見下面)。在你們的討論中,雙方都尖銳和正確地強調了問題的這一方面——爭取國有化鬥爭的方法,因此我毋須再多談它。
我僅指出 “小小”的一點。那些在靈魂上是君主主義者的人,能否認真地思考革命鬥爭呢?認為似乎王權在比利時是虛構,是嚴重的錯誤。首先,這個“虛構”是值錢的,它應該用經濟考慮來排除。但事情的主要方面不在這裡。在社會危機時代,幽靈往往會長出肉體,輸入血液。在德國由為希特勒鋪路的興登堡在我們眼前扮演的角色,在比利時可能由國王依他的義大利同事的榜樣和範例來扮演。比利時國王近期的一系列姿態明確地指出了這條道路。誰想進行反法西斯的鬥爭,就應該從消滅君主制的鬥爭開始。不允許社會黨在這個問題上藏在詭計和保留之後。
革命地提出戰略和策略問題,但根本不意味著我們的批評不應該跟著社會黨滲入它的議會避難所。新的選舉要在1936年才舉行:在此之前,資本主義反動和饑餓聯手三次扭斷工人階級的脖子。必須十分尖銳地對社會黨工人提出這個問題。為了加速新的選舉,只有一個途徑:通過轉變為阻礙議會議事的強烈的反對派使今天的議會無法履行其職能。不僅應該因王德威爾得、德·曼之流不發展議會外的革命鬥爭,還應為他們的議會活動絲毫不為準備、接近、實現他們自己的“勞動計劃”而鞭撻他們。在這個領域中的矛盾和虛假將最容易讓一般社會黨工人理解,但他還沒有成長到理解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
關於對中間階級的態度的問題,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因改良主義者想爭取小資產階級而指責他們,說他們以此走上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是可笑的。我們也想爭取小資產階級。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徹底成功的重要條件之一。但正如莫里哀[3]所說的,雖是捆柴,但各有不同。[4]街頭小販和貧農是小資產者。但教授、獲得勳章的中等官員、中級工程師也是小資產者,應該在他們之間進行選擇。資本主義議會(不存在其他的議會)導致律師、官員、記者先生們作為饑餓的手藝人、街頭小販、小官吏和半無產階級農民的潛在的代表。金融資本牽著小資產階級律師、官員和記者出身的議員的鼻子,或乾脆收買他們。
當王德威爾得、德·曼之流說把小資產階級吸引到計劃方面來,那他們指的不是它的群眾,而是它的潛在的“代表”,即金融資本的腐化的代理人。當我們說爭取小資產階級時,我們指的是把人民受壓迫的底層從它的潛在的政治代表那裡解放出來。由於小資產階級居民群眾的絕望處境,舊的小資產階級政黨(民主黨、天主教黨等)已經千瘡百孔。法西斯明白了這點。它過去和現在都不尋求與破產的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們”的聯盟,而是把群眾從他們的影響下爭取過來,即以自己的方式,為反動的利益,完成當年布爾什維克為革命利益而完成的那個工作。現在在比利時的問題正是這樣。小資產階級政黨或是大資本家政黨的小資產階級一翼註定要與議會制一起消失,後者曾為它們製造了必要的腳手架。整個問題在於,誰引領被壓迫、受欺騙的小資產階級群眾追隨自己:在革命領導下的無產階級,或是金融資本的法西斯代理人。
正如德·曼不想要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害怕可能會導致革命鬥爭的議會的大膽的反對派政策,他同樣不想和害怕真正的爭取小資產階級群眾的鬥爭。他明白,在它的深處隱藏著巨大的抗議、殘酷無情、仇恨的儲備,它們能夠變成革命激情,可怕的“過火行為”,即革命。為避免這種結果,德曼尋找議會盟友,受到重創的民主黨人、天主教徒、右翼的哥兒們,他需要他們作為抵禦可能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火行為”的支柱。我們應該善於在日常事實經驗中向改良主義工人解釋問題的這一方面。爭取無產階級與城鄉受壓迫的小資產階級群眾的緊密的革命聯盟,但反對與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和叛徒的政府內的聯合!
某些同志表達了這樣的意思,社會黨提出“勞動計劃”的本身應該會振奮中間階級,在無產階級消極的情況下,會方便法西斯的工作。當然,如果無產階級不進行鬥爭的話,那法西斯就會勝利。但這個危險不是由於計劃,而是由於社會黨的巨大影響和革命黨的軟弱。德國社會民主黨長期加入資產階級政府為希特勒開闢了道路。純消極地阻止布呂姆加入政府,同樣為法西斯的增長創造了前提。最後,在沒有相應的群眾革命鬥爭的情況下,宣佈對金融資本的進攻,必然會加速比利時法西斯的工作。因而,問題不在於計劃,而是在社會黨的叛變的職能和共產國際的致命的角色。但由於整體形勢,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命運,把“國有化”政策強加給了比利時妹妹,所以除了舊的危險外,還展現了新的革命機會。看不到它們是最大的錯誤。應該善於用自己的武器來戰勝敵人。
只有在不倦地對工人提出法西斯危險的條件下,才可能利用新的機會。為了實現任何一種計劃,應該維護和鞏固工人組織。因而應該首先保護它們免遭法西斯匪徒的攻擊。寄希望于民主政府,哪怕是社會黨領導的政府來拯救法西斯的危難,用法令來禁止它組織和武裝等,是最大的愚蠢。任何員警的禁止都於事無補,如果工人自己不學會對付法西斯的話。組織無產階級防禦,建立工人民兵隊伍是最緊迫和首要的任務。誰不支持這個口號,不實際貫徹它,誰就配不上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稱號。
* * *

現在還要說說我們對社會黨左派的態度。在此我最不想說任何蓋棺論定的話,因為我迄今沒有機會追蹤這個集團的演變。但近幾天我讀了的東西(斯巴克的系列文章,他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等),讓我產生了不好的印象。
當斯巴克應該說明合法和非法鬥爭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性質時,他把奧托·鮑威爾,即合法和非法的萎靡不振的理論家,當作權威來引用。“告訴我誰是你的老師,我就能對你說你是誰。”但我們把理論領域放在一邊,轉向緊迫的政治問題。
斯巴克把德·曼的計劃當作戰役的基礎,毫無保留地贊成它。可以說:斯巴克不想給王德威爾得之流現在就把事情搞到分裂地步的機會,把軟弱的、尚未組織起來的左翼驅逐出黨;斯巴克為了更好地跳躍,他先退了幾步。也許,斯巴克的意圖是這樣的,但評判一個政治家不是根據他的意圖,而是行動。斯巴克在代表大會上的謹慎的行為,他十分堅決地保證為完成計劃而鬥爭,他遵守紀律的聲明本身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注意到左派反對派在黨內的地位的話。但斯巴克還做了些其他的:他不僅在計劃的抽象目的上,而且在具體的鬥爭方法上,表達了對王德威爾得的道義上的信任和政治上與德·曼的團結一致。
斯巴克說,我們不能要求黨的領袖們公開地對我們說自己的行動計劃,自己的力量等,這些話帶有格外不能容忍的性質。為什麼不能?出於保密?但如果王德威爾得和德·曼有所保密的話,那也不是與革命工人反對資產階級,而是和資產階級政治家反對工人的秘密。是啊,誰也不要求在代表大會上公佈地下工作的秘密!需要提供動員群眾的總體計劃和鬥爭前景。斯巴克以自己的聲明幫助了王德威爾得和德·曼回避答覆最重要的戰略問題。在此完全有權說反對派領袖與多數派領袖反對革命工人的密謀。斯巴克被引上中派主義輕信的道路和“青年社會主義近衛軍”這一事實,更是加重了他的罪過。
在布魯塞爾聯盟的代表大會上就憲法和革命鬥爭作出了“左”的決議。決議很弱,它具有司法性,而不是政治性,它是律師寫的,而不是革命家寫的(如果資產階級破壞憲法,我們就……)。“左”的決議不是嚴肅地提出準備革命鬥爭的問題, 而是對資產階級提出文字威脅。但在代表大會上發生了什麼?在德·曼——我們知道,他認為革命鬥爭是有害的神話——的幾個最空洞的聲明後,布魯塞爾聯盟馴服地撤銷了自己的決議。如此輕易地滿足空洞和虛假的言詞的人,是不能認為是嚴肅的革命者的。懲罰很快降臨。第二天,《人民報》這樣注釋代表大會的決議,說黨將嚴守憲法框架,即將在金融資本在國王、法官和員警的協助下給它指出的框架內“進行鬥爭”。左翼的機關報《社會主義者行動報》真是因此而淚流滿面:須知昨天,就是昨天,對布魯塞爾決議還是“所有人”完全一致,為什麼今天可笑的哭訴!“昨天”欺騙左翼,是為了讓他們撤銷決議。而“今天”飽經世故的官僚機靈人給倒楣的反對派一個教訓。活該!這些事從來都是這麼做的。但這僅僅是花,果實還在後面。
社會黨反對派闡述極左的批評,只要這不讓它承擔任何責任,這已經不止一次了。但當負責的時刻(群眾罷工運動、戰爭威脅、國家政變的危險等)到來時,反對派立即放下旗幟,為劣跡斑斑的黨的領袖們提供新的信任貸款,以此證明,它本身與改良主義骨肉相連。現在,比利時社會黨反對派經受第一次嚴肅的考驗。只能說,它馬上就摔了大跟頭。我們應該認真和沒有成見地追蹤它今後的腳步,在批評中不誇大,別轉向荒謬的“社會法西斯”的嘰嘰喳喳聲,但別對這個集團的理論和戰鬥鍛煉抱任何幻想。為了幫助左派反對派的最優秀成員前進,應該如實地說出一切。
* * *
為了讓這封信能在1月14日會議前到你們的手上,我寫得很匆忙:它的不全面,也許還有闡述的不夠系統,都是由此而來的。在結束時,我允許自己表達熱烈的信心,即你們的討論將以能夠保證行動的充分一致的一致通過的決議而告終。整個形勢預先決定了你們的組織在最近一個時期的巨大增長。如果社會黨反對派的領袖們徹底投降的話,無產階級革命一翼的領導將完全落到你們的肩上。如果相反,改良主義黨的左翼前進,走向馬克思主義,你們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戰鬥的盟友和通向群眾的橋樑。在明確和一致的政策的條件下,你們的成績是完全有保證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比利時支部萬歲!
格·古羅夫
1934年1月9日

譯自網上下載的Письмо в редакцию «Peuple», 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3-1934年),托洛茨基著,施用勤譯。
[1] 德·曼(Hendrik de Man,1885-1953)比利時工党右翼領袖,1933年終止蕭條,旨在促進生產的《勞動計劃》的作者,它贏得了比利時勞工運動的支持。——英譯者注
[2] 斯派克(Paul-Henri Spaak,1899-1972)比利時社會黨領袖之一(1944年起),曾任外交大臣(1936-1937、1938、1939-1947、1949、1954-1957、1961-1966)和首相(1938-1039、1946、1947-1949)。1957-1961年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年輕時曾是“左派”,曾是比利時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左翼成員,曾與托洛茨基合作。——俄文網站編注
[3] 莫里哀(Jean Baptiste Moliere,1622-1673)法國喜劇作家、演員、戲劇活動家、舞臺藝術的革新家。把民間演出傳統和古典戲劇的成就結合在一起,創造了社會生活喜劇。作品嘲笑了貴族的等級偏見和資產者的局限性(如《可笑的才女》,1660;《女學者》,1672;《強迫的婚姻》,1664;《貴人迷》,1670;《心病者》,1673)。喜劇《答丟夫》(1664,一譯《偽君子》)揭露了僧侶的偽善面目。《吝嗇鬼》(1668)則揭示了金錢的腐蝕力量。1665年上演的《唐璜》因有無神論和自由思想而使他遭受迫害。莫里衣的遺產具有極大的價值:他所塑造的角色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對世界戲劇文學和舞臺藝術的發展產生很大影響。
[4] 此話出自莫里哀的劇本《美第奇》。——俄文網站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