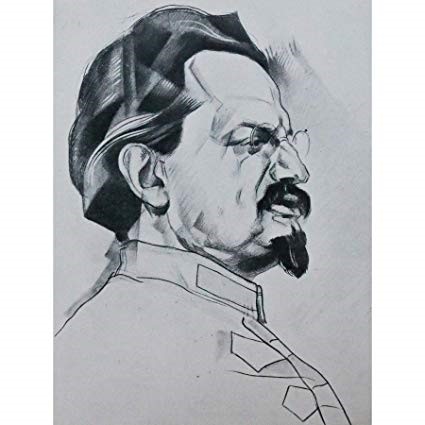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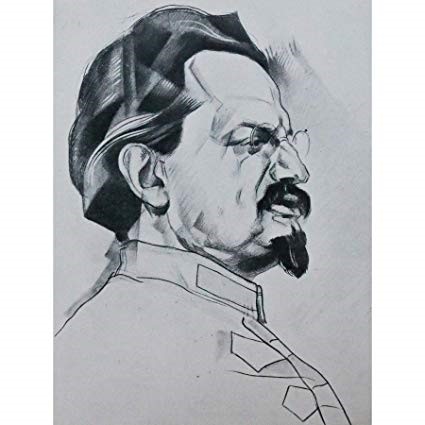
我們在過去的一篇文章中已經說過,法國社會黨的發展方向與國家發展方向相反:由於議會制被波拿巴主義所取代,後者代表的是在通往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個不穩定的階段,相反,社會黨是朝著與法西斯主義致命衝突前進。不過,是否可以賦予這個現在對法國政治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情況以絕對的、因而也是國際意義的性質呢?
不,真理永遠是具體的。當我們說在當前社會危機的條件下,社會黨和資產階級國家的發展道路背道而馳時,我們說的只是發展的總體趨勢, 而不是同一的機械過程。對我們來說,政治問題的解決取決於趨勢變成現實的程度。可以提出相反的原理,希望它不會在我們之中引起任何異議,即在我們時代,無產階級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黨是否能在發展進程給予它的短暫瞬間內,堅決地與資產階級國家決裂,並為反法西斯的決死戰鬥調整自己,為此做好準備。無產階級的命運可以取決於社會黨命運的可能性的本身,是作為國際無產階級領導黨的共產國際的垮臺和階級鬥爭異乎尋常的加劇的結果。
被中派主義推到一邊的改良主義傾向,像中派主義激進化的傾向一樣,由於符合資本主義和民主國家的整體危機,是不能不具有國際性的。但對於從在發展的現階段,在特定國家的社會黨中,這個傾向會如何折射這個問題中得出實際的,首先是組織的結論,是有決定性的意義的。我們制定的總的發展路線,只能指導我們的分析,但絕不預先得出它的結論。
在前法西斯德國,資產階級國家和改良主義的破裂的臨近表現為社會民主黨內的左翼的形成。但在群眾完全迷失方向的情況下,官僚機關足夠強大,能夠提前砍掉還很軟弱的左翼(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讓黨停留在保守和觀望政策的軌道上。同時,德國共產黨在“第三時期”[1]和“社會法西斯主義”的咒語和蠱惑下,用阿姆斯特丹的遊行[2] 來取代對群眾的革命動員,而在現實力量對比中,在沒有統一戰線政策的情況下,這種動員是無法實現的。結果是,強大的德國無產階級表明它無力給予法西斯政變以最輕微的抵抗。斯大林分子宣稱:這全是社會民主黨的錯!但他們以此承認,他們想成為德國無產階級領袖的野心沒有任何意義,只不過是空話吹牛而已。這個重大的政治教訓對我們表明,首先,甚至是在一個國家中有重大影響——在絕對和相對意義上——的共產黨,也不會在決定性的時刻有所作為,由於社會民主黨保持了集中它的保守抵抗前者的力量的可能性。讓我們把這點牢牢地銘刻在頭腦中。
這個基本歷史趨勢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法國折射出來。在特殊的民族條件和國際教訓的影響下,法國社會黨的內部危機經歷了遠比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相應時期更加深刻的演變。社會黨官僚不得不被迫對右進行打擊。不是開除的軟弱的左翼,像在德國的情況下那樣,我們見證了與更堅定的右翼(作為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即新社會黨的決裂。這兩個分裂以其對稱性最鮮明地突出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社會黨之間在演變中存在的重大區別,雖然這兩個黨有共同的歷史趨勢: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危機,改良主義的垮臺和資產階級國家與社會民主的決裂。
從上面指出的角度,必須對正在經歷危機不同階段的所有國家的社會黨的內部情況做出評價。但這個任務不在本文的範圍之內。讓我們只提一下比利時,那裏的社會黨已經被反動、腐敗的官僚——議會、市政、工會、合作社和銀行官僚——徹底束縛,現在它已陷入反對其左翼的鬥爭中,力求無論如何都別落後於自己的德國榜樣(威爾斯-塞弗林[3]及其一夥)。很清楚,是不能對法國和比利時得出同樣的實際結論的。
認為一方面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比利時社會黨的政策,另一方面是法國社會黨的政策,代表的永遠是兩個彼此水火不相容的類型,是錯誤的。在現實中,這兩個類型能夠並且會不止一次地彼此轉換。可以充滿信心地說,如果當時德國共產黨推行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的話,它會強有力地推動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激進化,德國的整個社會發展就會獲得革命性。另一方面,得到斯大林分子積極支持的法國社會黨的官僚會孤立左翼,讓黨朝退化的方向演變,這也是不能排除的;不難預見它的結果:無產階級的沮喪和法西斯的勝利。對比利時來說,社會黨實際上是無產階級的唯一政黨,沒有在社會黨的隊伍中決定性的力量和傾向的重組,勝利的反法西斯鬥爭是根本不能想像的。但不能事先預見所有的發展階段和形式。必須用手觸摸勞工運動的脈搏,每次都得出必要的結論。
上面所說的一切,對理解社會黨內部的演變對無產階級命運——至少在歐洲,對最近的歷史時期來說——的極端重要性來說,已經足夠了。如果我們回憶一下,1925年,共產國際在一份專門的宣言中宣稱,法國社會黨已經不復存在,我們就可以毫無困難地明白,在不肖之徒[4]的統治下的幾年中,無產階級,尤其是它的先鋒隊出現了多大的倒退!
對德國,共產國際已經承認——誠然是在事後,以負面的形式——它完全沒有能力進行反法西斯鬥爭,如果社會民主黨不加入鬥爭的話。對法國,共產國際被迫做同樣的聲明,但在事先,用的是積極的形式。對共產國際越糟糕,對革命事業就越好!
* * *
在未經說明的情況下拋棄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斯大林分子同時拋棄了革命綱領。他們對法國社會黨的領袖們說:“你們的條件就是我們的條件。”他們放棄了對他們的盟友的批評。他們乾脆為了這個聯盟而放棄了他們的綱領和他們的策略。不過,當問題是防禦共同的死敵時,而且聯盟的每一方追求的都是自己的生存利益時,防禦是不需要任何一方為這個聯盟付出任何東西的,每一方都有保留它自己的權利。斯大林分子的所作所為的性質似乎是想暗示社會黨的領袖們:“要求更多點兒,擠得更狠點兒,別不好意思;幫助我們盡快擺脫在現在的國際形勢下困擾我們莫斯科主人的尖銳口號。”
拋棄工人民兵的口號。宣佈爭取武裝無產階級的鬥爭是“挑釁”。在警察局長先生的監督下與法西斯分子分享“勢力範圍”不是更好嗎?這是所有組合中最有利於法西斯分子的:當被關於統一戰線的泛泛的話語催眠的工人參加遊行時,法西斯分子會增加他們的幹部和他們的武器儲備,會從群眾中吸引新的預備隊,在他們選擇的適當時機發起進攻。
這樣,對法國的斯大林分子來說,統一戰線是他們對社會黨投降的形式。統一戰線的口號和方法是對波拿巴政府的投降,後者又是在為法西斯主義開闢道路。通過統一戰線,兩個自保的官僚不無成功地保護自己免受“第三種力量” 的干擾。很快即將面對決定性事件的法國無產階級的政治狀況就是這樣。如果沒有群眾的壓力和社會黨內各派的鬥爭的話,這個狀況可能是致命的。
* * *
誰說第二和第三國際都註定滅亡,未來屬於第四國際,他表達的思想的正確性,已經被法國的當前形勢所再次證明。但這個本身正確的思想沒有告訴我們,第四國際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和在什麼期間內建成。它可能由第二和第三國際的統一所誕生——這在理論上是不能排除的,通過在戰火中的人員重組、進一步清洗和鍛煉隊伍的方法。它也可能通過社會黨內的無產階級核心的激進化和斯大林主義組織的分解而形成。這可能在反法西斯鬥爭和戰勝它的過程中形成。但它的誕生也可能會晚得多,在幾年之後,在法西斯勝利和戰爭造成的廢墟和斷壁頹垣中。對所有的博爾迪加分子來說,所有這些變化、前景和階段都沒有意義。宗派主義者生活在超時空中。他們忽視活生生的歷史過程,後者以同樣的方式回報他們。這就是他們的“平衡”永遠是零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者與這樣的政治漫畫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毋須說,如果在法國存在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強大組織,在當前的條件下,它就能夠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圍繞著它聚集的獨立軸心。但法國共產主義者同盟還未能成為這樣的組織。絲毫不想減輕領導的錯誤,但必須承認,同盟緩慢發展的主要原因是由國際工人運動的進程造成的,近10年來,它遭受的全是失敗和倒退。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思想和方法在每個發展的新階段上都得到了驗證。但作為一個組織的同盟,是否能夠期望它在日益迫近的結局來臨前的那段其間內在工人運動中佔據有影響的位置,如果不是領導位置的話?今天給予這個問題以肯定的答覆,意味著或是在頭腦中把結局推後了幾年,這與整個形勢相矛盾,或乾脆是寄希望於奇跡。
十分明顯,法西斯的勝利意味著所有工人組織的垮臺。將揭開歷史新的一章,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將在其中為自己尋找新的組織形式。在與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時期的性質緊密聯繫中,今天的任務應該具體地闡述如下:在無產階級的所有現存團體以及這些團體之間的力量的現有相互關係的情況下,如何盡一切可能防止法西斯的勝利?其中包括:同盟作為一個小組織,不能覬覦在我們面前展開的鬥爭中扮演獨立角色,但被正確的學說和寶貴的政治經驗武裝起來的同盟,在其中將佔據什麼位置,才能豐富統一戰線的革命內容?清楚地提出這個問題,實質上已經回答了它。為了積極促進革命重組和集中它的力量,同盟必須立即在統一戰線內佔據這個位置。在當前的條件下,它只有加入社會黨,才能佔據這樣的位置。
某些同志反駁說,但須知共產黨畢竟要革命得多。即便決定要放棄我們的組織獨立性,我們能依附不那麼革命的黨嗎?

這是主要的,更確切地說,是我們的反對者的唯一理由,它依據的是政治回憶和心理評價,而不是活生生的動態發展。這兩個黨都是中派主義組織,區別是:斯大林分子的中派主義是布林什維主義解體的產物,而社會黨的中派主義是改良主義解體產生的。它們之間還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區別。斯分子的中派主義雖然有令人震驚的左右搖擺,它是與強大的官僚階層的地位和利益密不可分的穩定的政治制度。社會黨的中派主義反映的是尋找走上革命道路的工人的過渡狀態。
在共產黨內,無疑有數千名有戰鬥力的工人。但他們已經被徹底搞糊塗了。昨天,他們準備與真正的法西斯匪徒並肩戰鬥,反對達拉第[5]政府。今天,他們悄悄地向社會黨的口號投降。[6]被斯大林分子訓練出來的聖-鄧尼斯的無產階級組織順從地向無產階級統一黨[7] 投降。復蘇共產國際的10年的嘗試和努力沒有取得效果。官僚表明它足夠強大,可以把它的破壞工作進行到底。
賦予統一戰線以純裝飾的性質,以“列寧主義”的名義加冕放棄基本革命口號,斯大林分子延遲了社會黨的革命發展。現在,在他們的雜耍般轉折之後,他們繼續扮演他們的制動器的角色。黨內制度今天比昨天更加堅決地排除了任何復蘇它的想法。
不能把法國社會黨和法國共產黨比成一塊布上的兩塊料:哪一塊布更好,哪一塊更結實?必須在每個黨的發展中看它,而且要考慮到它們在當前這個時期的動態的相互關係。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為我們的杠杆找到最有利的支點。
同盟加入社會黨能夠起重大的政治作用。法國有數萬無黨派的革命工人。他們中的不少人加入過共產黨;他們或是已經憤慨地退出,或是已經被開除。他們仍舊保持他們對社會黨的過去的態度,即不屑理它。他們同情或半同情同盟的思想,但未加入它,因為他們不相信在今天的條件下第三黨能夠發展起來。這幾萬革命工人留在黨外,而在工會內,他們也在黨團之外。
此外還應加上數百、數千名革命人民教師,不僅是統一聯合會的,還有全國工會的,他們可以成為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聯繫紐帶。他們留在黨外,對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都同樣仇恨。然而在最近一個時期,群眾鬥爭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地為自己尋找黨的管道。建立蘇維埃不是削弱,而是相反,加強工人政黨的角色,因為數百萬被蘇維埃聯合起來的群眾需要只有政黨才能提供的領導。
沒有絲毫必要把法國社會黨理想化,即把現存各種矛盾的它冒充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黨。但可以也應該把這個黨的內部矛盾指出來,作為它以後演變的依據,最終作為馬克思主義杠杆的支點。同盟能夠也應該給這成千上萬的革命工人、人民教師等作出表率,他們在當前的條件下仍有處於鬥爭潮流之外的危險。加入社會黨,他們可以極度加強它的左翼;他們可以使黨的整個演變更加富有成果;他們可以建立吸引“共產黨”的革命分子的強有力的中心,這樣就可以極大方便無產階級走上革命道路。
無須放棄自己的過去和自己的思想,但也沒有任何小團體的別有用心,明確地說出實情,那就是應該加入社會黨的必要性,不是為了巡迴演出,不是為了實驗,而是為了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嚴肅的革命工作。
1934年8月
譯自網上下載的Путь выхода, 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譯。

* 譯自網上下載的Путь выхода。
此文載1934年9月的La Verite《真理報》,署名CC,1934年9-10月的《新國際》,署名V。此文為發表而寫,但直到8月29日,同盟全國代表會議同意加入法國社會黨後,才在La Verite發表。在刊登此文的那期La Verite上,把它說成是法國社會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集團的文件。除解釋贊成加入的理由外,托洛茨基的文章還警告說,在法國與社會黨得出的結論,不能機械地運用到其他國家,每個國家的形勢都要具體考察。同時,他暗指加入策略也不必僅限於法國。同年晚些時候,他贊成加入比利時、西班牙社會黨,他同意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與美國工人黨合併為工人黨的決議,後者於1934年12月成立。一年多以後,於1936年初,美國工人黨決定加入美國社會黨。——英譯者注
[1] “第三時期”理論所謂的三個時期,是把1917年以後的世界革命形勢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從1917至1923年,是革命的高潮時期;第二時期從1924至1927年,是資本主義穩定時期;第三時期從1928年開始,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全面勝利的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即將總爆發,它已無力對付下一次經濟危機,從現在起,世界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此前一直處於守勢的共產國際將轉入全面反攻,階級鬥爭中的任何偶然事件都將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意義。斯大林炮製這個荒誕的理論,是為了彌補此前他與布哈林一起在國內外推行的右傾政策造成的災難——1927年秋的糧食徵購危機和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並標誌著他從極右轉向極左。然而經驗主義的搖擺帶來的都是災難,在第三時期理論指導下的德共在面對法西斯危機時,不僅不與社會民主黨結成統一戰線,反而集中火力打擊“社會法西斯”,使希特勒坐收漁人之利,於1933年上臺,也使人類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浩劫。——譯注
[2] “阿姆斯特丹的遊行”指的是斯大林主義組織(世界反戰委員會、世界反法西斯委員會等)的各種“戰線”的活動往往是在阿姆斯特丹發起或指揮的。它的兩次主要的代表會議一次於1932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召開,另一次於1933年6月在巴黎召開。它的典型的分支機搆是美國反戰反法西斯同盟,在人民陣線時期,它更名為爭取和平與民主同盟。——英譯者注
[3] 威爾斯(Otto Wels,1873-1939)和塞弗林(Carl Severing,1875-1952)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作為柏林的軍事指揮員,威爾斯在1919年鎮壓了斯巴達克起義,後來他領導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塞弗林曾任普魯士內務部長,於1932年7月被巴本免職。——英譯者注
[4] 不肖之徒是用來稱呼那些敗壞其老師的學說的人。托洛茨基用來稱呼列寧病重和逝世後打著列寧學生的旗號破壞列寧主義的人。——譯注
[5] 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1884-1970)法國激進黨領袖。1933-1934(有間斷)和1938-1940年多次出任部長和總理。1938年簽署了《慕尼克協定》。——譯注
[6] 相當多的共產黨員在1934年2月6日的法西斯分子和保皇分子的示威遊行中是與後者攜手進行鬥爭的,他們中的部分人是在共產黨領導的老兵組織旗幟下進行鬥爭的。這是暗指1931年8月的所謂的紅色全民公決,那時德國斯大林分子和納粹一起為通過投票推翻普魯士的社會民主黨政府而努力。——英譯者注
[7] 無產階級統一黨是一個短命的中派主義組織,它由被開除的共產黨員和前法國社會黨黨員組成。——英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