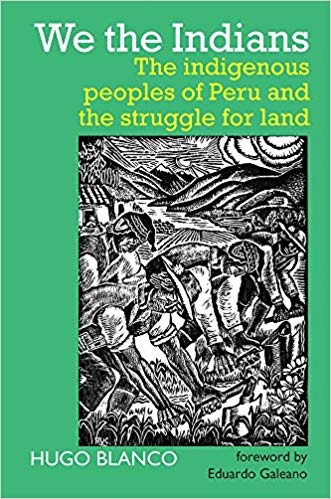
雨果·布兰科:从信奉托洛茨基主义到追寻土著力量
安德鲁·莱德
以下乃书评:《我们印第安人:秘鲁土著人民与土地斗争》,抵抗丛书、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默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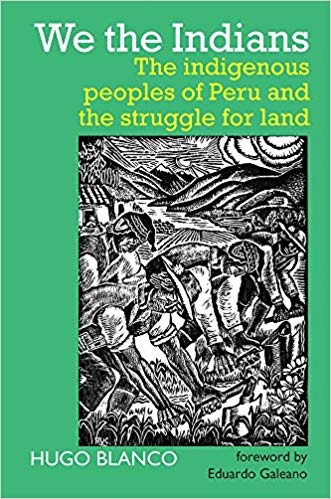
在关于革命潜力的当代思想上,雨果·布兰科是重要的人物。他的想法和实际践行包括了两个大观点:
第一,是托洛茨基主义传统,这个传统产生于俄罗斯工人革命的经验,产生于其对官僚堕落和背叛的重要批判,产生于其武装自卫以保护工人阶级自主权的建议。第二,土著人民长期和不断的抵制殖民者和企业家,因为后者为自己的利益而侵占土著人民的土地和生活设施。今天,土著人民不想同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马克思主义能否被扩展至满足土著人民的这种需要和愿望,是令人十分关切的问题。布兰科的工作是重要的例子,可用以联结这两个立场和方法。
《我们印第安人:秘鲁土著人民与土地斗争》,由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和默林出版社出版,布兰科的这本新英文文集,展示他长期的行动和研究。该书收入的记录包括他的组织工作、监禁和绝食,以及他对土著小区价值观和生态经验的思考。作品还包括他与伟大的秘鲁小说家何塞·玛丽亚·阿尔盖塔斯(José María Arguedas)的通信,以及他对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立场的强烈批评。
雨果·布兰科是20世纪60年代伟大的游击队领袖之一。然而,他的战略明显不是当时风行整个南美大陆战略的变种,后者的灵感来自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模式。布兰科自己指出,他拒绝用小型机动战斗队的办法,迅速对抗和推翻政府。相反,布兰科呼吁进行防御性的武装斗争,以维持安第斯地区土著地区的自治权,以便在这些地方上进行长期的民主社会革命。在这方面,布兰科部分继承列昂·托洛茨基部分想法,托洛茨基提出人民民兵是适当的社会主义军事组织形式。在20世纪60年代,布兰科是第四国际的成员,他认为这是更大的革命战略的时刻,最终可以推翻政府,并呈现社会主义的新生产模式的前奏。布兰科的做法也预示后来萨帕蒂塔民族解放军(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采用的方法。
萨帕蒂塔主义者(Zapatistas)也反对在土著社会民主进程采用有利于民兵的游击战略。同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一样,布兰科最终决定,夺取国家权力的目标并不在目前的政治视野中,接受一种或多或少是永久的防御姿态将更加现实和有效。这样明显远离托洛茨基早先的做法,后者坚持与国家权力发生不可避免的对抗,并需要与其它地方的工人阶级组织保持一致。
这为马克思主义斗争和土著斗争的衔接提出了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张工人阶级是革命变革的主体。在一些教条式的提法中,这可能导致农村组织和社会集体边缘化,可以被看作是过去的残余。然而,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坚持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呈现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先河,这些秩序不需要被分解成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生产关系。何塞·卡洛斯·马里埃特吉(José Carlos Mariétegui)对土著传统小区(ayllu)空间进行分析,认为这是抵抗资本主义积累和规则的领域,也是社会主义革命行动的潜力基地。布兰科实际上发掘了马里埃特吉洞见的潜力。
然而,这留下了土著斗争如何影响城市混血工人阶级前景的问题。布兰科自己说,国家和城市之间的对立已经过时,因为新自由主义使整个民众陷入贫困。这表明,工人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团结仍然是基本目标;土著农民小区不是从根本上脱离了资本进程,而是构成工人阶级的不寻常的阶层,这种阶层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特别不同。因此,这保留对国内和国际革命意识的更广泛认识,而不是接受地方主义。
因此,这与土著身份的认同问题有关。布兰科致力于保卫克丘亚(Quechua)和艾马拉(Aymara)人民。与马里埃特吉(Mariátegui)一样,他认为他们继承共产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特有的剥削性个人主义和分工不相容。因此,这是对民族特殊主义的部分辩护;这部分人口特别容易受到资本主义掠夺的影响,但也善于进行抵抗和斗争。重要的是,布兰科拒绝根据遗传来定义这个群体,相反,他认为这种身份认同是文化的,他认为这种文化是对外来者开放的,外来者可以改变,可以接受土著价值观。他写道,“蓝眼睛的金发女郎"可以参与印地安小区,而血脉遗传是不必要的。布兰科本人是混血儿;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形容他为"一个聪明、疯狂的人,他决定成为印地安人,尽管他不是,结果却是最为印地安的人。”我认为,因此在这里,捍卫土著的特殊性提出了更广泛的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不仅"尊重差异"的可能性,而且通过关注这些小区保存维持的经验和知识,改变整个社会秩序。
布兰科有时坚持民主人文主义。例如,他坚持认为,“人类的斗争可以概括为争取真正民主的斗争。”对他来说,土著传统小区(ayllu)是直接民主的核心,克服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代议异化。然而,在理解布兰科的人文主义时,也应该知道他深刻尊重非人类的社会成分。他写道:
我求你,为了我们的蛇类姐妹、我们的蟾蜍兄弟、我们的甲虫兄弟、为了树木和植物、蝴蝶、为了帮助我们生存,阻止他们谋杀亚马逊雨林。
他甚至谈到"属于人类的耻辱"。对布兰科来说,社会主义的视野不止于人类;他不同意现代欧洲关于人类解放即是统治自然的观念。在这方面,他与托洛茨基在1924年的著名评论大相径庭,托洛茨基认为人会根据自己的品味改善自然。布兰科说“强烈渴望成为一只豺狼、蝰蛇、蟾蜍,任何只为食物而猎食的动物,任何从不施暴的动物。”布兰科关于革命的思想,可以这样理解为挑战,即根据土著文化必有的某些认识论见解,重新塑造人类、民主和革命的概念。
秘鲁人类学家玛丽索尔·德拉·卡德纳(Marisol de la Cadena)通过与马里亚诺·图尔波(Mariano Turpo)长达十年的对话,阐明这种世界观,马里亚诺·图尔波是克丘亚(Quechua)思想家,他见过布兰科,对其委身于政治信念受到启发。玛丽索尔·德拉·卡德纳发展土著的 “地球存在物” (earth beings) 概念,即生态和物质存在物具有自身的能力、脆弱性和欲望。她还知道,土著传统小区(ayllu)不仅是人类民主和集体所有权的世界,也是人类深刻意识到其与非人类成分相互作用的地方。我认为,阅读布兰科和马里亚诺·图尔波的文章,有助于我们理解土著生活世界如何呈现新的政治可能性,可以辩证地融入马克思主义传统。
近年来,我们看见很多人纷纷努力,把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同土著思想和实践结合起来。罗克珊·邓巴尔-奥尔蒂斯(Roxanne Dunbar-Ortiz)、劳尔·齐贝奇(Raúl Zibechi)、阿尔瓦罗·加西亚·里纳(Álvaro García Linera)、杰弗里·韦伯(Jeffery R. Webber)和格伦·肖恩·库尔特哈德(Glen Sean Coulthard)为两者结合作出贡献。雨果·布兰科深刻的身体力行和自我牺牲,以及长年的努力,使他成为特别有价值的传奇人物。他传承托洛茨基在俄罗斯背景底下产生的见解,具有拉丁美洲游击战的经历,以及追寻本世纪具有新活力的土著斗争精神。他行文零散无章——乃源于实际的斗争;但值得我们努力发掘他的探索成果,以丰富当前的政治与文化理解能力。
本文译自《国际观点》, 2018年12月17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