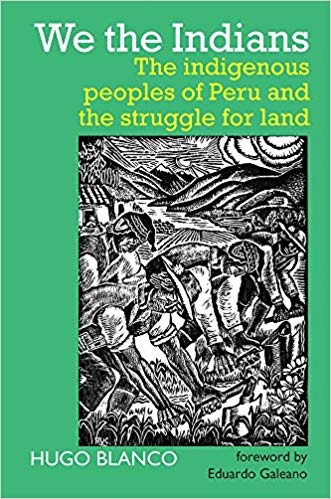
雨果·布蘭科:從信奉托洛茨基主義到追尋土著力量
安德魯·萊德
以下乃書評:《我們印第安人:秘魯土著人民與土地鬥爭》,抵抗叢書、國際研究與教育研究所、梅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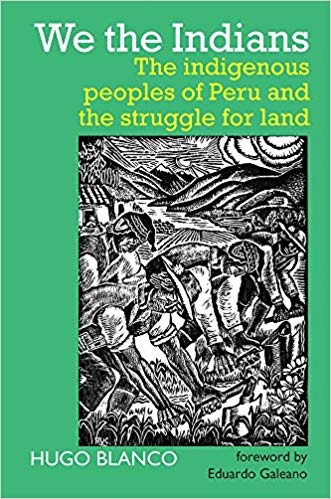
在關於革命潛力的當代思想上,雨果·布蘭科是重要的人物。他的想法和實際踐行包括了兩個大觀點:
第一,是托洛茨基主義傳統,這個傳統產生于俄羅斯工人革命的經驗,產生于其對官僚墮落和背叛的重要批判,產生於其武裝自衛以保護工人階級自主權的建議。第二,土著人民長期和不斷的抵制殖民者和企業家,因為後者為自己的利益而侵佔土著人民的土地和生活設施。今天,土著人民不想同化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馬克思主義能否被擴展至滿足土著人民的這種需要和願望,是令人十分關切的問題。布蘭科的工作是重要的例子,可用以聯結這兩個立場和方法。
《我們印第安人:秘魯土著人民與土地鬥爭》,由國際研究與教育研究所和梅林出版社出版,布蘭科的這本新英文文集,展示他長期的行動和研究。該書收入的記錄包括他的組織工作、監禁和絕食,以及他對土著社區價值觀和生態經驗的思考。作品還包括他與偉大的秘魯小說家何塞·瑪麗亞·阿爾蓋塔斯(José María Arguedas)的通信,以及他對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所闡述的新自由主義立場的強烈批評。
雨果·布蘭科是20世紀60年代偉大的游擊隊領袖之一。然而,他的戰略明顯不是當時風行整個南美大陸戰略的變種,後者的靈感來自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模式。布蘭科自己指出,他拒絕用小型機動戰鬥隊的辦法,迅速對抗和推翻政府。相反,布蘭科呼籲進行防禦性的武裝鬥爭,以維持安第斯地區土著地區的自治權,以便在這些地方上進行長期的民主社會革命。在這方面,布蘭科部分繼承列昂·托洛茨基部分想法,托洛茨基提出人民民兵是適當的社會主義軍事組織形式。在20世紀60年代,布蘭科是第四國際的成員,他認為這是更大的革命戰略的時刻,最終可以推翻政府,並呈現社會主義的新生產模式的前奏。布蘭科的做法也預示後來薩帕蒂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採用的方法。
薩帕蒂塔主義者(Zapatistas)也反對在土著社會民主進程採用有利於民兵的游擊戰略。同副司令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一樣,布蘭科最終決定,奪取國家權力的目標並不在目前的政治視野中,接受一種或多或少是永久的防禦姿態將更加現實和有效。這樣明顯遠離托洛茨基早先的做法,後者堅持與國家權力發生不可避免的對抗,並需要與其他地方的工人階級組織保持一致。
這為馬克思主義鬥爭和土著鬥爭的銜接提出了重大問題。馬克思主義思想主張工人階級是革命變革的主體。在一些教條式的提法中,這可能導致農村組織和社會集體邊緣化,可以被看作是過去的殘餘。然而,眾所周知,馬克思本人堅持認為有這樣的可能性,即前資本主義社會可能呈現社會主義新秩序的先河,這些秩序不需要被分解成佔主導地位的城市生產關係。何塞·卡洛斯·馬里埃特吉(José Carlos Mariétegui)對土著傳統社區(ayllu)空間進行分析,認為這是抵抗資本主義積累和規則的領域,也是社會主義革命行動的潛力基地。布蘭科實際上發掘了馬里埃特吉洞見的潛力。
然而,這留下了土著鬥爭如何影響城市混血工人階級前景的問題。布蘭科自己說,國家和城市之間的對立已經過時,因為新自由主義使整個民眾陷入貧困。這表明,工人階級不同階層之間的團結仍然是基本目標;土著農民社區不是從根本上脫離了資本進程,而是構成工人階級的不尋常的階層,這種階層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觀特別不同。因此,這保留對國內和國際革命意識的更廣泛認識,而不是接受地方主義。
因此,這與土著身份的認同問題有關。布蘭科致力於保衛克丘亞(Quechua)和艾馬拉(Aymara)人民。與馬里埃特吉(Mariátegui)一樣,他認為他們繼承共產主義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特有的剝削性個人主義和分工不相容。因此,這是對民族特殊主義的部分辯護;這部分人口特別容易受到資本主義掠奪的影響,但也善於進行抵抗和鬥爭。重要的是,布蘭科拒絕根據遺傳來定義這個群體,相反,他認為這種身份認同是文化的,他認為這種文化是對外來者開放的,外來者可以改變,可以接受土著價值觀。他寫道,“藍眼睛的金髮女郎"可以參與印地安社區,而血脈遺傳是不必要的。布蘭科本人是混血兒;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形容他為"一個聰明、瘋狂的人,他決定成為印地安人,儘管他不是,結果卻是最為印地安的人。”我認為,因此在這裏,捍衛土著的特殊性提出了更廣泛的社會轉型的可能性;不僅"尊重差異"的可能性,而且通過關注這些社區保存維持的經驗和知識,改變整個社會秩序。
布蘭科有時堅持民主人文主義。例如,他堅持認為,“人類的鬥爭可以概括為爭取真正民主的鬥爭。”對他來說,土著傳統社區(ayllu)是直接民主的核心,克服資本主義國家固有的代議異化。然而,在理解布蘭科的人文主義時,也應該知道他深刻尊重非人類的社會成分。他寫道:
我求你,為了我們的蛇類姐妹、我們的蟾蜍兄弟、我們的甲蟲兄弟、為了樹木和植物、蝴蝶、為了幫助我們生存,阻止他們謀殺亞馬遜雨林。
他甚至談到"屬於人類的恥辱"。對布蘭科來說,社會主義的視野不止於人類;他不同意現代歐洲關於人類解放即是統治自然的觀念。在這方面,他與托洛茨基在1924年的著名評論大相徑庭,托洛茨基認為人會根據自己的品味改善自然。布蘭科說“強烈渴望成為一隻豺狼、蝰蛇、蟾蜍,任何只為食物而獵食的動物,任何從不施暴的動物。”布蘭科關於革命的思想,可以這樣理解為挑戰,即根據土著文化必有的某些認識論見解,重新塑造人類、民主和革命的概念。
秘魯人類學家瑪麗索爾·德拉·卡德納(Marisol de la Cadena)通過與馬里亞諾·圖爾波(Mariano Turpo)長達十年的對話,闡明這種世界觀,馬里亞諾·圖爾波是克丘亞(Quechua)思想家,他見過布蘭科,對其委身於政治信念受到啟發。瑪麗索爾·德拉·卡德納發展土著的 “地球存在物” (earth beings) 概念,即生態和物質存在物具有自身的能力、脆弱性和欲望。她還知道,土著傳統社區(ayllu)不僅是人類民主和集體所有權的世界,也是人類深刻意識到其與非人類成分相互作用的地方。我認為,閱讀布蘭科和馬里亞諾·圖爾波的文章,有助於我們理解土著生活世界如何呈現新的政治可能性,可以辯證地融入馬克思主義傳統。
近年來,我們看見很多人紛紛努力,把馬克思主義革命傳統同土著思想和實踐結合起來。洛葛仙妮·鄧巴爾-奧爾蒂斯(Roxanne Dunbar-Ortiz)、勞爾·齊貝奇(Raúl Zibechi)、阿爾瓦羅·加西亞·里納(Álvaro García Linera)、傑佛瑞·韋伯(Jeffery R. Webber)和葛籣·肖恩·庫爾特哈德(Glen Sean Coulthard)為兩者結合作出貢獻。雨果·布蘭科深刻的身體力行和自我犧牲,以及長年的努力,使他成為特別有價值的傳奇人物。他傳承托洛茨基在俄羅斯背景底下產生的見解,具有拉丁美洲游擊戰的經歷,以及追尋本世紀具有新活力的土著鬥爭精神。他行文零散無章——乃源於實際的鬥爭;但值得我們努力發掘他的探索成果,以豐富當前的政治與文化理解能力。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 2018年12月17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