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集中概述了1931年至1945年時期發生在中國的運動。它是準備可能出版的、更大的有關中國托洛茨基主義故事的一部分,但卻是重要的一部分。 簡單地說,這是發展、鎮壓和分裂的故事。 這是飽受各方十五年攻擊的故事,還涉及到政治理論上的,有時帶有個人性質的孤立的內部爭端。要反思這個運動的悲慘經歷,沒有一個時期比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合適了。
關鍵字:托洛茨基主義(Trotskyism),中國共產主義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China),陳碧蘭(Chen Bilan),弗朗克·格拉斯(Frank Glass),彭述之(Peng Shuzhi),鄭超麟(Zheng Chaolin)

張開在1937年加入中國托洛茨基運動,當時他是上海的一名年輕學生。 在戰爭年代,他在上海被日本人拘捕和拷打。這位廣東中山人, 九十五歲,是一個以“耄耋老人”為主要成員之運動的“耄耋老人”之一。 這些人包括20世紀70年代後期少數從中國監獄釋放的人。 所有這些人都曾積極致力於挑戰中央政權的政治鬥爭而受難,這個政權或者是蔣介石國民政府,或者是1949年後的中共中央政府(見:Zhang, 2015年;Zhang,1994)。
1925年至1927年間,在莫斯科學習的中國學生中埋下了反對派種子,但這種反對派的正式成立,僅在1928年這些學生中的許多人回國後才發生。斯大林主義者對托洛茨基和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 的攻擊也早早移植到了中國輿論場中。
直到托洛茨基關於中國問題的著作問世,提供給一些黨員使用,中國左派反對派的基礎才得以建立。
到1930年,有四個不同的團體聲稱堅持托洛茨基政治觀點。 他們是“我們的話”[Women de hua];“無產者”[Wuchanzhe];“十月社” [Shiyue she] 和“戰鬥社”[Zhandou she]。
所有團體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和參與度,各自都有自己的出版物(Kagan[卡根],1969:46-69;Sheng Yueh[沈越],1971:164-83;Miller[米勒],1979:161-5;Benton[本頓],1996:29-35)。
許多年輕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對陳獨秀和彭述之的老一輩深感不信任,常常稱之為“陳彭集團”。[3] 例如,據說彭述之對於年輕活動家持高高在上的姿態。這些攻擊只不過加劇了已經存在的分歧(Zheng,1997:244;Wang,1991:145-9:Peng,2016:318-20)。這些差異在許多方面成為運動中持續多年的摩擦因素。

當陳彭集團於1930年初開始出版“無產者”雜誌時,來自共產黨內的同情人數在增加。卡根估計,在1931年,甚至在走向統一之前,就有五百人的規模(Kagan,1969:132)。
中共利用四個團體之間的爭端,圖謀削弱其任何吸納聚集成員的努力。列昂·托洛茨基成為中國左派反對派統一的主要推動者。自1929年末以來,他與各個團體定期通信。每個組織都認為自己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的“真正”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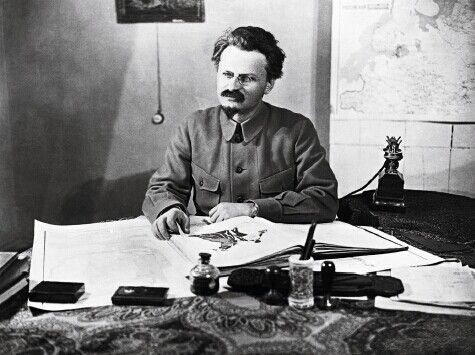
托洛茨基在1929年12月22日的信中,回應了“我們的話”小組的聲明:
關於陳獨秀集團,我非常瞭解其革命時期的政策, 那就是斯大林 - 布哈林 - 馬丁諾夫的政策,實質上就是右翼孟什維克的一個政策。
但是,N同志[劉仁靜]給我寫了一封信,說陳獨秀根據自己革命經驗採納的立場,相當接近我們的立場。 不言而喻,這只能受到歡迎。 不過,你在信中,斷然糾正了N同志的資訊。 你甚至認為,陳獨秀並沒有違反斯大林的政策,而後者是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混和物。 但到目前為止,我唯讀了一篇陳獨秀的綱領宣言,所以無法在這個問題上發表自己的看法(Evans and Block,1976:428)。
當他們要向前邁進時,他就會挑戰那些批評,提供更大的政治清晰度。 這是“國際反對派的政策,並不與任何特定的中國左派反對派站在一邊”,因為“我們的任何材料都未顯示有嚴重分歧存在而需要繼續分裂”。在信的結尾,他強烈推動團結,認為它應該是“真誠的”,並以“共同原則”為基礎。(Evans and Block,1976:441)
最後,為團結統一,組織了一個談判協調會,由四個小組的代表組成。 他們在1930年夏季和初秋試圖制定一個議程。在協調會的每次會議上各個組織提出不同的意見,致使談判拖延。新老兩代革命者之間的分裂,繼續是一個主要的障礙(Wang,1991:143-4; Peng,2016:318-20)。
最終,“無產者”派別向另外三個派別的成員發了一封公開信。 它駁斥了對其派別及其部分成員的不實指控。 它還回顧了一些分裂現象,以及一些個人的派別活動。 最後,它呼籲做出更多努力以便獲得沒有以前那些小爭端的統一。在團體和個人之間仍然存在某些政治問題需要解決,唯一成功的統一將是一個具有原則性的(“無產者”[Wuchanzhe],1930年)統一。
在最近的採訪中,彭述之承認,他認為在達成原則性統一之前,需要更多的時間進行討論。 王凡西則認為彭的立場,是完全反對統一的,是在要求所有其他派別解散併入“無產者”小組。彭反對把他的立場如此特徵化,認為他只是比陳獨秀更加謹慎而已(Wang,1991:148-9;Zheng,1997:248-50;Peng,2016:320-2).[4]
最終,在1931年1月8日的信中,托洛茨基為團結統一作了一個更強的結論。 他直接指出:
首先,我會說,在研究新文件時,我終於相信,在進入統一之路的各個團體間,原則上沒有任何區別。 在戰術中有細微不同,在未來,依據事件的進程,可能會發展成差異。 然而,沒有理由假設這些意見分歧必然與以前分組的線條相吻合。...
親愛的朋友,現在就須把你們的組織和刊物團結起來! 我們不能長期拖延統一的準備工作,因為那樣做,不用想就知道,那會造成人為的差異(Evans and Block,1976:492)。
他繼續說,“毫無疑問,明天以後的日子,會有新任務出現,帶來新的分歧。 沒有這個,革命黨的發展是不可能的。”他提醒中國同志們,中心重點應該始終放在具體的條件上(Evans and Block,1976:498)。
這些通信至少暫時平息了反對派內部的一些爭端。 統一會議於1931年5月1日開幕,開了三天多。 中國左派反對派現在取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China (CLC)][5] 托洛茨基1929年的文件“中國政治形勢與布爾什維克 - 列寧主義反對派的任務”(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Tasks of the Bolshevik-Leninist Opposition)被同盟採納為其綱領基礎(Trotsky,[托洛茨基],1947:139;Evans and Block,1976:402-8)。 這並沒有結束爭端和分裂,只是讓它們暫停一段時間。 表面上看,共產主義同盟很小,但其行動能力很高,因為其成員中經驗豐富的前黨幹部的比率很高。[6]
2.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CLC)領導班子的首次被捕和監禁
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成立的三周內,它遭到了國民黨(GMD)當局的第一次打擊。 1931年5月24日晚,上海的軍事當局在一個“叛徒”的幫助下,逮捕了九人同盟中央委員會中的六人。 陳獨秀得以逃脫,因為情報部門不知道他當時的地址。 彭述之由於從“一位同志在軍事總部的朋友”而獲得的最後消息,避免了被逮捕(彭,1976)。
王凡西是被捕者之一,他詳細描述了這次被捕的情況和這第一次監禁的實情((Wang F., 1974: 29;Wang, 1991: 162-7)。
據陳碧蘭介紹,“叛徒與蔣介石特務攜手合作。 特務在公園的入口處、劇院、貨商店、主要街道交叉處等候。 如果一個同志遇到了一個叛徒,他就會被便衣跟蹤並被逮捕(Ch'en,1980:32-3。另見Wakeman,1995:132-6)。
不久之後,其他的逮捕也接踵而至。 彭述之、陳獨秀、宋靜秀,這些僅有的還未被捕的中央委員會成員被迫轉入地下,不定期地在上海換地方。
3.日本軍國主義進入爭端
1931年9月18日,中國的內部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直接影響了共產主義同盟的增長和影響力。
當天夜晚,在瀋陽北部發生了爆炸事件,破壞了一小段鐵路,這是滿洲日本陸軍官員陰謀的一部分。 以此為藉口,日本軍隊‘在幾個小時內’就控制了瀋陽。 這只是日本對中國領土長達十四年的入侵佔領的開始。 雖然國際社會幾乎沒有注意到這個大事件,但日本方面這一舉動的直接結果是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意識的覺醒(Paine,2014:13)。[7]
國民政府雖然對這個事件作出了溫和的回應,但這些行為使中共在其仍然存在的地方激動了起來,也讓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餘下來的人及早採取行動,在城市組織群眾運動。
這個時期,同盟的努力主要是通過兩個期刊的發行,鼓動人心。首先,火花 [or Spark, after Iskra] 是一本地下雜誌,上面刊登餘下來的同盟領導人的信件和文章,以及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譯。
在最早的‘火花’ 期刊中,有一期出版於第一次“上海事變”之日,同盟呼籲中共中央成員要求蘇聯通過共產國際施加其影響力,援助中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他們挑戰該黨,要它利用民族革命鬥爭,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防止對蘇聯的攻擊。他們主張重新動員城市職工運動,並要求從村一級起進行選舉,選出國民(或制憲)大會。蘇維埃地區的武裝力量應該與工人運動聯繫起來,反對日本和國民政府。最後,同盟呼籲中共內部各派圍繞著這些努力而團結起來(Shi Fan[石凡],1932年)。
同盟的其他期刊,一個公開的週刊“熱潮”[Re Chao]也呼籲武裝群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據彭述之介紹,這一期刊在普通讀者中,包括在中國共產黨的讀者中,具有很大的影響。這可能是王明(陳紹禹)實行的政治組織政策的結果((Ch’en, 1980:33;Peng,1972;Peng,,1976)。
自1929年陳獨秀等人被驅逐出中共以來,在李立三的領導下,中共對持不同政見者的負責人繼續實行宗派主義指控。
事實上,李立三本人已經按共產國際代表帕維爾·米夫(Pavel Mif)的要求,被逐出了黨的領導層。李先生被控為“半托派”。隨著王明的興起,在帕維爾·米夫(Pavel Mif)的幫助下,這種做法被強化,導致了黨內更高程度的分歧(Chang,1972:2:136,143;Saich,1996:285-8)。
至於日益增長的日本帝國主義行為威脅而發展的政治問題,對此,陳碧蘭聲稱,王明對抗日運動的宗派態度,以及後來對國民黨左翼領導下的十九路軍的宗派態度,走向一個奇怪的極端。 在黨的機關報‘紅旗’上,他鼓吹紅軍在農村與日本人戰鬥,但反對武裝群眾,不支持十九軍抗擊日本的戰鬥,(Ch’en, 1980: 14-15)。
中共官方政策的這兩個方面的結合,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極大不滿,特別是在上海。 這使得許多黨員與共產主義同盟作更多的接觸,對有關政策的討論,使得一半以上的中共上海支部進入托洛茨基運動。 這包括“幾十個重要的黨小組、郵政、電廠和紡織工人”(同上,Stranahan,1998:85-9)。
彭述之負責組織有關黨員參與各種討論小組。最終,公共租界內的黨員投入運動,中共上海支部成為共產主義同盟的一個分支。那時,光是上海就有三百多人。彭在1972年寫信給理查·卡根指出,‘因為這些活動,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第一次能夠成為工人的堅強基礎,帶領他們在這個時期獲得許多罷工勝利。’這樣一來,共產主義同盟置身於抗日群眾運動中,又能夠超越上海,進軍北京、武漢、南京、廣州、香港等城市(Peng,1972;Peng,1976)。
中共 “紅旗週報”以特別的敵意回應了同盟這一意想不到的增長。 1932年4月8日的一篇文章,呼籲黨員學習和效仿斯大林對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處理方法,將他們稱為“孟什維克”,避免同作者所說的“列寧主義”相連。該作者說,托洛茨基主義者是“社會法西斯分子,為反對蘇聯共產黨,共產國際和蘇維埃的資產階級報紙寫文章。”指控清單還有:
中國托派主義者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武裝國民黨和其他反革命團體… 托洛茨基主義者利用郵政服務,以共產黨“左派”的名義寫信給警方,要求他們關閉我們的組織… 他們也向國民黨告密,使我們的組織被摧毀,我們的同志被逮捕。這證明了托洛茨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
根據這位作者的說法,在中共組織內仍然存在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殘餘,“我們必須在理論和組織上與這些殘餘進行鬥爭” (Huang Juan, 1932: 13-15)。
這場鬥爭似乎優先於當時對日本侵略軍的任何實際抵抗。 對以前受尊敬的黨領導者和積極分子的指控,使黨內的普通黨員對托洛斯基主義產生了某種好奇心。共產主義同盟明確表示,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這些攻擊事件並不輕率。 他們讓黨在各個方面,在政治和理論上參與其中(Shi Fan,[石凡] 1932年)。
有意義的是,同盟的底層基礎多半是工人所在的城市,而中共已經轉向農村,從而躲避蔣介石的壓迫。 當然這也意味著同盟很容易受到國民黨及其西方盟友的攻擊,更不用說越來越多的日本人攻擊了。
4.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領導人遭到逮捕、審判和監禁
1932年10月15日星期六下午,改組後的共產主義同盟中央會議在一私人住宅舉行。由於陳獨秀不舒服,彭述之擔任主席。突然,據彭說,“這個地方被警察包圍了”。這次會議的所有五名成員都被捕,所有書籍和其他文件都被沒收走了(Wang,1973;Peng,1976;Peng,2016: 332-3)。
當天下午,警方查得了陳的下落,將其逮捕,同時另有五人被捕。在接下來的兩天內繼續逮捕,直到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大多數主要幹部都被監禁。
這個大規模的圍捕引起了各地報紙的關注。例如,據“中國評論”報導,陳獨秀和“他的親信彭述之”被捕。據報導,這些囚犯於十月二十日抵達南京,立即被帶到“戰時軍事管制部拘留”,等待審判(中國評論,1932:5:43)。
陳獨秀在知識界是知名的公眾人物,新聞界密切關注這一案件。由於擔心軍事法庭立即把這些人處以死刑,中國社會中一些對陳友好的著名人物向蔣介石發電報,要求在民事法庭公開審理這個案件。據“中央日報”報導,審判前的調查將需要兩到四個月的時間。結果,直到1933年4月14日(被捕之後的六個月),這次公開審判才在南京開始(Wang,1973:第一部分)。
開幕當天,有八、九十人擠進法庭。對十二名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指控列在“中國評論”發表的一份報告中:“被告人被控兩項罪名,即:(1)煽動傳播動亂性宣傳,(2)組織旨在危害共和國的團體;觸犯了關於危害國家罪的緊急處罰法的第2條和第6條”(同上,“中國評論”,1933:6:2;又見Qiang, et al.., 1982: 160-91)。
審判持續了一個星期,最終判決於1933年4月26日發表。陳和彭被判處十三年監禁,剝奪公民權利十五年。他們判刑的嚴重程度反映了這個事實,即他們是共產主義同盟的領導人,他們把審判作為批評國民政府的公共論壇。然而,上訴到高等法院後,他們的刑期減少到八年(Ch’en,1980:36; Qiang,et al.,1982:198-209)。
再次,隨著更多同盟人被監禁,運動沒有了中央組織。這使得香港、北京、南京、武漢、浙江、杭州、廣州、廣西等地的分支自行其是,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保存自己和實施行動。
5. 無中心的運動(1933-37年)
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受到這些幾乎致命的打擊的時候,中國的政治和軍事情況進一步惡化。 1932年3月,日本成立了“滿洲國王朝”[8],這是其控制中國領土之持續企圖的一部分。到1933年5月,對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領導層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審判結束後,日本在北方控制的地域更大。持續到1936年華北運動,也在1933年扎實地展開( Paine,2014: 25-34, 36-9;見Benton, ,1992 and 1999)。
為了根除共產黨勢力,蔣介石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圍剿行動”,延伸到1932年和1933年。他認為,在對日本人採取有效的軍事行動之前,必須摧毀共產運動。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對中國農村和城市革命運動的真正潛力的承認 (Paine,2014:70-6)。
雖然同盟沒有組織中心,但仍有個人和團體願意在可能的情況下冒險進行組織和鼓動活動。此外,同盟期刊在1933年至1937年期間繼續出版。
據王凡西等人介紹,1932年至1934年間,保持活動的人物之一,就是還在上海的陳其昌。他和其他幾個人一直在出版‘火花’雜誌,還有一系列介紹托洛茨基主義立場的小冊子。這些剩餘的活動家,包括兩個“外國同志”,追隨國際托洛茨基運動的活動,通過外部接觸獲得材料(Wang,1991:171; Hinson,2003:123-40; Benton,2015:102-9)[9]
C.弗蘭克·格拉斯是來自南非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於1931年抵達中國,目的是以其任何可能採取的方式説明中國的運動。到1934年,他與陳其昌取得了聯繫。他曾擔任新聞記者,並在這艱難的歲月裡用其大部分工資來協助舉步維艱的托洛茨基運動。有趣的是,是格拉斯(王凡西給他取的中國名字為李福仁)使得哈樂德·以撒(Harold Isaacs)同情這個運動的。(Hinson,2003: 240n23, 83-6)
以撒也作為新聞記者來到中國,並於1932年,以“組織外”的方式,即用他的言論,與中國共產黨迅速取得聯繫。他發行了‘中國論壇’(China Forum),一本反映共黨官方中國事務觀點的英語雜誌(Isaacs,1934:76:7)。
他對共產黨不再抱有幻想,因為他發現嚴重的扭曲和誇張是中國以及國外共產主義宣傳的特徵。起初他把這些'歸結於‘個人的無知或無能’,但是他很快意識到,這是共產國際通過中共中央特意所作的政策決定。
以撒寫信給中共中央,辭去‘中國論壇’的工作,在信中,他指責中央退出城市勞工階級中心,把一些勞工領袖帶入了‘蘇區和紅軍。’
事實上,把最有覺悟和最進步的工人階級成員調離工人階級環境,並把他們送到蘇區,這種通常做法,是轉移錯誤焦點的良策,因為該錯誤的本質是癱瘓城市的工人階級運動(同上)。
在他努力批評國民黨及其做法時,遭遇到反對。他未被允許報導對陳獨秀等人的審判。黨要求他只發表對陳的攻擊,以證明國民黨的做法是正確的。他拒絕了。由於這些和那些原因,以撒決定關閉‘中國論壇’。黨要求他交出印刷設施,但他拒絕了。(同上)[10]
王凡西、陳其昌、弗蘭克·格拉斯繼續出版‘火花’雜誌,還有名為‘鬥爭’的新雜誌,據王介紹,這份雜誌‘到1936年秘密發行了兩百到三百份’。王也承認,弗蘭克·格拉斯在幫助維持運動的發展上,起了關鍵作用,而且他自己犧牲巨大(Wang,1974:30)。
這兩個期刊的發行,使得運動獲得新增長,包括香港在內,托洛茨基主義者在香港也出版了自己的雜誌,名為‘火星’(同上)。
然而,隨著這些發展的徵兆,王在一九三七年五月被國民黨警察逮捕。他們監視弗蘭克·格拉斯的住所,跟蹤‘任何訪問過他的人’。直到那年十一月,在南京遭到日本人的嚴重轟炸後,王才被釋放。格拉斯也在這個時候離開了中國去美國旅行,並同托洛茨基一起去墨西哥做訪問(同上,Hirson, 2003:140-2)。
這個運動又一次受到壓力,需要尋找新途徑,以便在沒有中央組織的情況下繼續運作。
6. 關於第二次統一戰線的論戰
到1936年下半年,由於臭名昭著的“西安事變”,人們呼籲建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第二次統一戰線”。蘇聯推動此事,因為它有助於防範來自其東部邊界的日本攻擊。在內部存在分歧的情況下,中共仍然接受了此計劃(Paine,2014:90-104;Sheng,1997:57-62; Wang,1991:218-20)。
在‘鬥爭’雜誌中,共產主義同盟照樣質疑中共與國民黨發展更密切合作關係的努力。正如蘇聯所宣導的那樣,這本雜誌認為,“在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下,相信‘一個國家先實現社會主義’的紳士們,失去了大腦,完全失去了對無產階級國際革命的信心,他們完全放棄了階級鬥爭的基本策略。”在西安事變之前,同盟批評毛澤東再次與中國資產階級聯手(鬥爭,Dou Zheng,1936年1月10日)。
1936年8月10日,毛澤東向救國會四名成員發了一封冗長的信,聲言‘向你們和全國人民致意,我們同意你們的聲明、方案和要求,真誠希望與你們和任何願意參與這一鬥爭的組織或個人合作,按照你們的建議和要求,進行共同抗擊日本人、拯救國家的鬥爭。’(Schram,1999年:295)。儘管南京政府的“圍剿”在繼續進行,毛澤東說:
在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際,我們不願繼續任何內戰屠殺同胞。如果他們不攻擊我們,如果他們不干涉打擊日本人的國軍,我們就不會攻擊南京中央軍隊或其他軍隊…我們願意與任何軍隊、任何政黨、任何派別合作,只要他們贊成准許抗日、反賣國賊和愛國運動的完全自由。(Schram,1999:296)。
緊接此後,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強烈譴責毛澤東的立場:
這是共產黨和紅軍領導人,給銀行家章乃器、教育家陶行知、生活書店老闆鄒韜奮、上海法科大學教務長沈鈞儒的信。誰會相信中國的工農大眾會遵從這四個人的方案,並通過他們,遵從蔣介石的方案呢?這是什麼意思?它表現了中國斯大林黨對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全面投降。這是對基層黨員利益的根本排斥! (鬥爭, Dou Zheng,1936年11月15日)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遭遇內戰和外部威脅,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活動分子被普遍視為失敗者,甚至是外人和“叛徒”。 他們一直堅持反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策,同時也試圖組織工人成為革命力量。
同盟從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角度批判了‘第二次統一戰線’的觀念,認為‘這個統一戰線是在共同綱領下無產階級各黨派的政治合併,意在對付敵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沒有共同利益,只有不斷的衝突。’這是試圖重申1925年至1927年的歷史失敗,並強調所有人民的‘民眾陣線’和一個真正的“統一戰線”之間的區別(鬥爭,Dou Zheng,1936年7月15日)。 [11]
7. 釋放,新的可能性,新的分裂
這就是陳獨秀和彭述之在1937年8月從南京監獄釋放出來時的政治現實。監禁歲月給這兩個人沉重壓力。彭先生的弟弟道之病死於監獄而未經治療。他們的友誼和同志關係在監獄中受到很大的壓力,現在兩人之間有深刻的分歧。
在監獄期間,關於蘇聯的性質,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制度的概念,陳對一些托派主義信條,在看法上有了根本性的分歧。在監獄期間,他和彭就這些問題交換了意見。彭堅持其稱之為“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Lin, et al., 2012: 250-61;Peng,1983: 85-105;Chen, 陳,2010: 449-66;Peng,2016: 340-2)。
他們從監獄釋放後,陳前往武漢,在那裡繼續與運動保持遠距離接觸。 彭終於回到了妻子和女兒生活的上海,希望能夠重振共產主義同盟(Zheng,張,1989:1012-19; Peng,2016:355-6)。
11月在上海召開了同盟臨時會議。那些還在地下的人和新近從監獄中釋放的人開會討論群組織的未來。早先的全國會議於1935年末或1936年初舉行(Glass,1935年;Wang,1991:175-8;Hirson,2003:133-4)。
這次1937年的會議通過了一項支持國民黨人進行抗日武裝鬥爭的決議,但批評國民政府的政治基礎。會議還選舉了“臨時中央委員會”,決定繼續出版 ‘鬥爭’雜誌(Peng,1972; Peng,2016:362-3)。
王凡西於十一月被釋放後,他首先前往武漢,同陳獨秀待了一段時間。據王介紹,陳先生當時心情沮喪,但政治觀念仍然清楚,陳建議說,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不應該試圖重建組織,而應該與所謂的“民主”黨派,如救世會、民主同盟和農工黨,這些當時被稱為“第三黨”的黨派合作。 王先生不同意這一建議,拒絕代表陳參加這些組織的會議, 而是前往上海,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取得聯繫,重新加入了‘鬥爭’雜誌編輯委員會(王,1974:31)。
再次,這一時期的運動又有了新的增長。地區組織在上海、北京、廣州、香港以及廣西和浙江等省重新建立。在彭述之被監禁期間,陳碧蘭發展了友人,因而獲得了必要的資金,可用於設立期刊出版單位。一個新的刊物‘動向 ’現在可以公開發行了。此外,在此期間,同盟成員鄭超麟、王凡西將托洛茨基的作品翻譯成中文,為該組織籌集資金(Ch’en,1980:37; Wang,1991:229-31)。
隨著同盟的重組和增長,中共的指責更加強烈,中共基地現在延安,毛澤東擔任其軍事委員會主席。以王明[陳少禹]、周恩來、博古為首的長江局位於武漢。對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政治攻擊來自這些中心。
反托派運動最喜歡的一個策略,是惡毒地將同盟及其成員描繪成“服務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法西斯主義者”或乾脆就是“法西斯主義者”,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同盟活躍在日本戰線後面或日本佔領區內,這些指控,對運動以外的許多人來說,似乎是合理的。此外,任何個人,只要稍有一點漢奸或“叛徒”(由中共認定的)嫌疑,都被自動地譴責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即使他們與同盟沒有任何聯繫(Chen,et al. 1939; Jun Xing,2005)[12]
張慕陶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表明這些指控是如何進行的。在1938年的一段時間裡,張是中共最喜歡攻擊鞭打的男子。在王明康生等人的演講和文章中,他被譴責為“托派叛徒”。據彭述之介紹,像三十年代中國的許多其他年輕人一樣,張在北京學習期間,受到托洛茨基主義思想的影響。張從未加入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但去過山西,在那裡擔任綏靖主任閻錫山的秘書,被毛澤東譴責為“叛徒”。所以,通過將張過去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興趣與“叛徒”聯繫起來,中共發明了“托洛茨基主義叛國分子”(社會主義訴求,Socialist Appeal, 1938:2:10;彭,1977)的指控。
中共當局也指責彭述之和陳獨秀是接受日本金錢出賣國家的人。 彭在湖南的朋友看到過的中共聲明,稱他住在上海‘在日本軍隊的保護下,日本士兵守衛著他的家。’當這位朋友回到上海發現這不是真的時候,‘他的同情立刻離開了中共轉向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對中共如此囂張表示憤慨。’即便是周恩來也拒絕了對彭或陳獨秀的這種指責(Peng,1976)。
對陳獨秀的追究有另一個效果,他們把許多中國學者的憤怒引到了中共集體的頭上。1938年在廣州發表了一系列譴責中共詆毀陳的文章。雷宇桐發表聲明,要本著杜威委員會(Dewey Commission)的精神,追求真相,進行這一工作,杜威委員會成立於1937年,目的是調查莫斯科審判中的斯大林指控(Lei,1938)。
這個文集中的一個重要例子,是鄭學稼“給中共黨員的公開信”。鄭教授被指為“托派叛徒”之一,雖然自從1927年以來他一直聲稱自己不是任何黨派或派別的成員。中共稱他為“南京政府的喉舌”和“法西斯主義者”,因為他呼籲他們結束反對國民黨的暴動。鄭先生回答說,“由於法西斯主義是在垂死帝國主義勢力中產生的一個政治現象,中共似乎分不清牛馬”。(同上,Zheng,1976)。
國際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密切關注發生在中國的這些事件,特別是因為這些攻擊明顯是斯大林共產國際發動的。美國的托洛茨基新聞社定期發表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導(Socialist Appeal, [社會主義訴求],1938:2:22)。
反對中共誹謗運動的一個有效途徑,是各個城市工人運動中同盟的自身行動。例如,在1938年八月底和九月初,為反對日本海運,在香港太古碼頭進行的為期十天的罷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成員是直接參與者。‘社會主義訴求’報導了罷工及其結果:
在工人的心目中,第四國際在罷工之前和期間的活動,完全駁斥了斯大林主義分子對其所謂“叛國分子”和“日本間諜”的譭謗,以至於中國斯大林主義者覺得不得不用他們著名的格別烏(G.P.U. )辦法讓第四國際從現場消失。
他們與香港警察當局密切合作,給後者提供虛假文件,他們終於成功地跟蹤了我們的一些同志,使這些同志立即被逮捕並遭刑求(Socialist Appeal, ‘社會主義訴求’,1938:2:36)。
中共難以解釋,為什麼所謂的“叛徒”會深深地參與工人的抗日鬥爭。 在大多數情況下,黨只是無視同盟的活動,而不是更多地報導那些活動。 然而,他們毫不猶豫地利用地方當局,或者英國當局或者中國當局,來幫助鎮壓同盟。 這樣做有一定的互利關係,因為英國當局並不希望周圍的托洛茨基主義分子也同共產黨或國民黨那樣。 人們可能懷疑,地方當局和中共暗地裡有一個協議,作為“統一戰線”的一部分,也即,為了更有效地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社會的和平是必要的(Chu,2010:34-5)。

8. 對戰爭態度的不同:導致1941年的分裂
不久之後,在這些多重攻擊的壓力下,隨著國際關係的重大轉變,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內部的爭論也重起。到1939年秋天,隨著“斯大林-希特勒條約”的簽訂,對中國和歐洲戰爭的不同意見成了三方分裂的基礎。這次辯論討論的三方,總的代表是同盟的四位高層領導:陳獨秀、彭述之、王凡西、鄭超麟。
陳認為,這場戰爭是民主與法西斯之間的根本鬥爭,沒有任何特別的階級內容。他認為“民主”國家的革命者應該無異議地支持戰爭行動。在支持國民黨戰爭行動的同時,共產主義同盟也應該停止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批評(Wang,1991:228; Kuo,1975:225-38; Lin, et al. 2012:436-40)。

王凡西說,他在1940年末寫過一文:“太平洋戰爭與中國抗戰”,發表在‘鬥爭’雜誌上。他對戰爭的基本立場是:
一旦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當時由國民黨控制)就必須被視為更廣泛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國民黨作為美帝國主義的小盟友必將會調整其計劃,以適應美國最高司令部的大戰略,結果,民族解放運動必將從屬於美國取代日本成為東亞主導國家的野心,… 我們對國民黨領導的戰爭的態度 ,應更多地符合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宣導的革命政策。 我們應更加重視革命的勝利,而不是戰爭的勝利(Wang,1991:234)。
據王介紹,在討論該文時,編委會表示同意該文觀點,編委包括陳其昌、鄭超麟、樓國華、劉家良。 他把這個立場稱為“革命失敗主義”,根據他對這一概念的理解,那基本上意味著革命綱領不應該在戰爭期間被擱置,而應該盡全力把革命的控制推向整個國家。 他也稱這為“革命勝利主義”,因為“只有革命才能真正戰勝帝國主義”。鄭超麟同意王,也採納了這個立場,雖然王認為他們之間存在有小差異(Wang,1974:32; Zheng,1997:254; Benton,1996:86-7)。[13]
這次辯論以彭述之為代表。 他的主要論據見於1941年4月4日的文章“對兩條路線的鬥爭”中。 他回顧了列寧關於黨內鬥爭中的立場,認為自共產主義同盟創立以來就存在於成員之間的分歧,只是因為日本侵略事件的壓力,導致整個運動的孤立而加劇。 他回顧了自1934年以來他自己與陳獨秀之間差異的發展,將陳代表的“戰爭”觀點描繪成“右派的”,因為彭認為,他們完全無原則地屈從國民黨的勢力(Peng,1983:138-71)。[14]
彭進一步認為,“革命失敗主義者”的觀點是“極左的”。 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這種反對,反映了對列寧“革命失敗主義”和不斷經濟革命理論概念的全面誤解。 他聲稱要保衛托洛茨基關於戰爭的基本方法,其中包括考慮到美國的潛在角色(同上)[15]
他回應了這是向蔣介石投降、放棄階級鬥爭的指責。認為:
泛泛而談“革命失敗主義”,不區分剝削者國家和被剝削的國家,是為帝國主義者服務而製作的一個痛苦漫畫。在遠東,我們有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而日本就在我們眼前把它轉變成一個殖民地國家。 日本的鬥爭是帝國主義和反動的,中國的鬥爭是解放和進步的(Evans and Block,1976:568)[16]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怎麼會成為“解放與進步”鬥爭的一部分呢? 難道工農運動反對他們,即便不多於,可也不會少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吧? 托洛茨基的回應令人信服:對蔣介石,他的政黨,或整個中國的統治階級,我們都不會有幻想,就像馬克思恩格斯對愛爾蘭和波蘭的統治階級毫無幻想一樣。 蔣介石是中國工人和農民的劊子手。 但是,今天他被迫為了中國的殘存獨立而與日本進行鬥爭。明天他可能背叛。是有可能的。很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今天他正在努力鬥爭。 只有懦夫、歹徒或白癡才會拒絕參與這場鬥爭(Evans and Block,1976:568)。
革命者必須察看任何戰爭中的交戰方所持的國際立場:
日本和中國乘的不是同一架歷史飛機。 日本的勝利將意味著中國受奴役,意味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結束,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可怕的增強。恰恰反映,中國的勝利意味著日本發生社會革命,也就是說,意味著中國的階級鬥爭,在不受外來壓迫束縛的情況下,自由發展(同上)。
而且,以下作為對“我們的中國朋友”(即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進一步警告:
明天與國民黨同盟的格別烏(GPU)將代表中國朋友作為 “失敗主義者”和日本的代理人。他們中最好的人,以陳獨秀為首,可以在國內和國際上被出賣和陷害。 有必要強調,第四國際站在中國一方反對日本。而且同時我要補充,它沒有放棄其綱領或獨立性(Evans and Block,1976:570-1。重點在原著)。[17]
當然,托洛茨基的這些觀點,都是出現在其遭暗殺之前,在抗日戰爭擴大到世界範圍之前。 隨著情況的變化,共產主義同盟(以及更廣泛的第四國際)內部的辯論也在繼續。 隨著托洛茨基的死亡,國際運動中的早期分裂也嚴重了(Drucker,1994:106-38,148)。[18]
10. 理論、戰略和戰術差異導致分裂
1941年7月13日,在共產主義同盟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一項題為“我們對德- 蘇戰爭和即將來臨的美日戰爭的態度與政策”的政治決議。這一決議指出,“所有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後國家,包括蘇聯在內,將捲入即將來臨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國抗日戰爭與蘇聯反德戰爭的命運現在已經聯合起來了”。該文件還討論了少數人關於“失敗主義”的一些立場,指出了他們的不足之處。同盟多數人為戰爭的行動提出了一長串的建議(中國共產主義同盟,1941年)。
例如,他們要求完全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領導罷工,武裝抗日,並且向各黨成員,除了叛國者以外,推進其政治綱領。他們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建立鄉村農民協會,以及徵收土地。對於他們與中共的關係,同盟認識到政治上必須繼續批評該黨,但對於目前的抗日戰爭和蘇聯捍衛戰,有必要在實際行動中同其進行合作。最後,決議討論了游擊隊的組織,對日軍的騷擾行動,以及打擊南京汪精衛的具體行動(同上;Liu,2005:286-90;Li Fu Jen,1941;Fourth International, 1941年)。
這些少數人是怎麼來的?首先,有人認為,陳獨秀實際上與托洛茨基運動有分歧。這是多年來的爭論源頭,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也是這樣的。早在1948年,王明遠[王凡西]寫道:
我們可能會猜測,如果陳沒有去世,他可能會把餘年投入到第四國際的事業。對此,我們不能給出這個問題的明確答案。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也說他與托洛茨基主義的分裂,不能被認為是最後確定的(Wang,1948年)。
一些學者認為,陳的最後幾年,是同任何激進運動最後切割的幾年,回歸到了以前的民主觀點。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不知道陳繼續與共產主義同盟維持遠距離的聯繫,直到1941年的大會。他們呈現了一個孤獨怨恨者的圖畫,一個不滿現狀的流亡者,直到1942年5月27日,他六十二歲離世(Hu Shi,1964年,Zheng,1980:200-1;Feigon,1983:220-4)。
王凡西和鄭超麟的少數派與同盟保持了一段時間的聯繫。王在回憶錄中說:
我們對那次會議的準備與進行都不滿意,但接受了它的結果,我們自安於少數派地位。不過我們要求一個權利,即在機關報《鬥爭》上開闢一討論欄,雙方繼續進行問題的闡述。(Wang,1991:235-6)。
新中委會拒絕了我們的要求。我們乃自行出版內部刊物,後來我們命名這個內部刊物為《國際主義者》。這導致多數派的譴責。到1941年5月,共產主義同盟經過十年脆弱的統一,現在真正的分裂了(Liu,2005:279-96; Chen,2010:473-4; Peng,2016:390-1)。
到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佔領香港和上海,控制了中國更多的地方,共產主義同盟及其分裂團體的實際影響力大為受限。同盟中央組織與地方單位之間的溝通被徹底切斷。所有的活動都變得當地語系化了。
據王凡西介紹,發動和組織工人中的工作仍在繼續,比如在上海設立學校。 他的小組還設法繼續出版了‘國際主義者’雜誌一段時間,大多數文章由鄭超麟撰寫。王批評彭的多數派讓“鬥爭”雜誌在抗戰期間停刊。至於“游擊活動”,王指出,它們並不算太多。 但是,他確實提供了有關托洛茨基主義者對日本軍隊作各種鬥爭嘗試的一些資訊:
一些同志以個人身份加入江蘇南北的抗日游擊隊,還有些不知名的人,曾經在游擊隊裡起過相當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兩批中國托派人士,由廣東的陳仲禧領導,以及由山東的王昌耀、張穎新夫妻領導,成功組織了幾千人強的游擊隊,與日本人打了近兩年。
在日本軍隊,或日本軍隊加上中共隊伍無緣由的襲擊下,這些團體最終被消滅。(Wang,1991:238;Liu, 劉[劉平梅],2005:177-245)
對於同盟的中央領導,許多幹部因日本控制大城市而受到逮捕。 許多人被處決。 在上海,彭述之及其家屬在“恐怖條件”下進入地下生活。 他通過改名(陳松濤)在大夏學院謀得教師職位,而妻子則改名為陳碧雲,並以此名發表關於婦女和青年的文章。 彭通過他的教學,開始與不瞭解他真實身份的左傾學生進行接觸。 有些學生甚至去他家訪問了他和他的妻子,他們在那裡討論政治和社會問題(Peng,1976; Chen,2010:476-502; Peng,2016:394-403)。
在1927年的失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在中國托派運動中,發生了很多事情。在初創佈局啟動後,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統一運動開始了20世紀30年代的十年,帶有一些樂觀的氣氛。不久之後,國內勢力的壓迫,侵略戰爭的開始,加上內部爭端,使同盟陷入困境,發展與團結起伏不定。 (Peng,1947;Wang,1948a;Wang,1948b)。
上海等地的托洛茨基‘中心’現在被日本帝國佔領,領導幹部分散在中國各地,同運動的聯繫被切斷了。至少在戰爭期間,這個運動多少有些癱瘓,儘管沒有完全失效。
關於運動在戰時和戰後,能有些什麼作為的爭論,多年來一直在持續。有人傾向於低估托洛茨基主義者在戰時的實際參與程度,對此責難,張開認為,在戰爭期間,托洛茨基主義者所做的很多事情遠不止宣傳,許多人在城市和戰場上犧牲自己,進了監獄,遭受折磨和死亡。最近,他詳細介紹了上海、廣東、廣西、山東、江蘇、浙江、溫州、香港、重慶等地的托洛茨基主義實際活動。這是一場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斷遭受攻擊之運動的記錄。
在詳細回顧了托洛茨基主義者在這段時期遭受的一切壓力和攻擊後,張總結道:
在這些最困難的環境下,這個運動能夠在工人階級中維持一個革命中心,為未來的復蘇作好準備。這一堅決的努力必須得到承認(Zhang,張,2005)。
隨著戰爭的結束,在內戰中將有新的希望、新的機會,但並沒有保障,讓這個運動可以從十五年不斷的攻擊、中斷和內部糾紛中恢復過來。
(2016年9月11日收到,2016年10月11日修改,2016年10月23日定稿)
Benton, Gregor. 1992. Mountain fires: 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 1934-193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山火:紅軍在南方的三年戰爭,1934-1938。加州大學出版社。
. 1996. China’s Urban Revolutionarie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otskyism, 1921-1952.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中國城市革命者: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史研究,1921-1952年。 新澤西:人文出版社。
. 1998. Edited and Translated. Chen Duxiu’s Last Articles and Letters, 1937-1942.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編譯。陳獨秀最後的文章和信件,1937-1942年。
檀香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
. 1999.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1938-194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新四軍:長江淮河一帶的共產黨抗日,1938 - 1941年。 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
. 2015. Edited. Prophets Unarmed: Chinese Trotskyists in Revolution, War, Jail, and the Return from Limbo.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編輯:徒手先知:處於革命,戰爭,監禁中的中國托派及其從地獄邊緣的返回。萊頓:Brill出版社。
Chen, Bilan. 2010. Zaoqi Zhonggong yu Tuopai: Wode geming shengya huiyi. Hong Kong: Tiandi chubanshe. 陳碧蘭。2010. 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
Ch’en, Pi-lan [Chen Bilan]. 1980. ‘Looking Back Over My Years with P’eng Shu-ts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New York: Monad Press. 陳碧蘭。1980. ‘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刊載於掌權的中共,紐約Monad 出版社
Chen, Shaoyu, et al. 1939. Tuopai zai Zhongguo. Jinhua, Zhejiang: XinZhongguo chubanshe. 陳紹禹等,1939. 托派在中國,金華,浙江:新中國出版社
Chu, Cindy Yik-yi. 2010. Chinese Communists and Hong Kong Captialists: 1937-1997.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中國共產主義者和香港資本主義者:1937-1997.紐約:帕戈理夫 麥克米蘭出版社
Coble, Parks M. 2015. China’s War Reporters: The Legacy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國戰爭記者:抗日戰爭傳說。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
Communist League of China. 1941. ‘Women dui De-Su zhanzheng ji pojinde Ri-Mei zhanzheng zhi taidu he zhengce,’ Zhongguo gongchan zhuyi tongmoeng zhi zhengzhi zhuzhang. Guomindang Investigation Bureau.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1941. ‘我們對德蘇戰爭暨迫近的日-美戰爭之態度和政策,’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之政治主張。國民黨調查局
Drucker, Peter. 1994. Max Shachtman and His Left: A Socialist’s Odyssey through the ‘American Centur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馬克斯·沙特曼及其左派:一個社會主義者穿過“美國世紀”的艱苦跋涉。 新澤西:人文出版社。
Evans, Les and Russel Block. 1976. Edited. Leon Trotsky on China. New York: Monad Press. 編輯。列昂·托洛茨基論中國,紐約:Monad 出版社
Feigon, Lee. 1983. 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陳獨秀:中國共產黨創始人。 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1. ‘The Danger of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China and the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ists,’ International Bulletin. Volume I Number 5. 第四國際 1941,“美國干預中國的危險和第四國際成員的任務”國際公報。第一卷第5號
Glass, Frank. 1935. Minutes of Meeting of Provision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of China (Bolshevik-Leninists).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臨時委員會會議紀要(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 馬克思主義互聯網文件案。
Glass, C. Frank. 1990 [1939]. ‘The Communist League of China,’ Revolutionary History. Volume 2 Number 4.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革命史。第2卷 第4期
Hirson, Baruch. 2003. Frank Glass: The Restless Revolutionary. London: Porcupine Press. 弗蘭克·格拉斯:無休止的革命。倫敦:Porcupine出版社
Hu Shi. 1964. ‘Chen Duxiu zuihou duiyu minzhu zhengzhi de jianjie xu,’ Zhuanji wenxue. Volume 5 Number 4. 胡適。‘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敘,’傳記文學。第5卷第4期
Huang Juan. 1932. ‘Sidalin tongzhi de xin yu fan Tuoluosiji zhuyi de douzheng,’ Hong zhoubao. Number 35. 黃娟。1932。‘斯大林同志的心與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虹週報,第35期
Isaacs, Harold. 1934. ‘I Break with the Chinese Stalinists’. The New International. Volume 1 Number 3. “我和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決裂”。 新國際。 第1卷第3期。
. 1985. Re-Encounters in China: Notes of a Journey in a Time Capsule.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 1985年。再遇中國:記時間梭艙之旅。 香港:聯合出版社。
Joubert, J.P. 1988 [1985]. ‘Revolutionary Defeatism’ Revolutionary History. Volume 1 Number 3. ‘革命失敗主義’革命史,第1卷第3期
Jun Xing [Zhang Kai]. 2005. ‘Shixuejie pingfan ‘Zhongguo Tuopai shi Hanjian’ cuoan’ Shiyue Pinglun. Volume 32 Numbers 2/3. 張開,“史學界平反‘中國托派是漢奸’錯案”,十月評論。第32卷第2/3 期
Kagan, Richard C. 1969. The Chinese Trotskyist Movement and Ch’en Tu-hsiu: Culture, Revolution and Poli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esis. 中國托派運動和陳獨秀:文化,革命與政治。 賓夕法尼亞大學。 論文。
Kuo, Thomas C. 1975. Ch’en Tu-hsiu (1879-1942)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South Orange: 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 陳獨秀(1879-1942)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南奧蘭治:Seton Hall大學出版社。
Lei Yutong. 1938. Edited. Zhongguo gongchandang gongji Chen Dusiu dengde fanxiang. Guangzhou: Xindong chubanshe. 雷雨桐,1938,中國共產黨攻擊陳獨秀等的反響。廣州:心動出版社
Li Fu Jen [Frank Glass]. 1941. ‘Report on the Chinese Situation and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Bulletin. Volume I Number 5. 李福仁。1941。《中國形勢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活動情況的報告》,國際公報,第一卷第5期。
Lin Zhilang, Wu Mengming and Zhou Fujiang. 2012. Edited. Chen Duxiu wannian zhuzuo xuan. Hong Kong: Tiandi. 林致良, 吳孟明, 周履鏘。陳獨秀晚年著作選,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
Liu Pingmei. 2005. Zhongguo Tuopai dang shi. Hong Kong: Xinmiao. 劉平梅。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
Matgamna, Sean. 1998. Edited. The Fat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st Texts of Critical Marxism. Volume 1. London: Phoenix Press. 俄羅斯革命的命運:批判性馬克思主義的迷失文本。 倫敦:鳳凰出版社。
Miller, Joseph T. 1979.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Trotskyism: The Role of a Permanent Opposition in Commun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Thesis.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政治:共產主義永久反對派的作用。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論文。
Paine, S.C.M. 2014. The Wars for Asia, 1911-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亞洲戰爭,1911 - 1949年。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
Peng Shuzhi. 1947. ‘Trotskyism in China’ Fourth International. Volume 8 Number 7 彭述之,1947,‘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第四國際。卷8第7期
. 1966. Professor Robert A Burton Interviews. 1966年。11-13 August. 1966年,Robert A Burton教授訪談。8月11-13日
. 1972. Letter to Richard C. Kagan. 12 January. 1972年。給Richard C. Kagan 的信。
. 1976. Joseph T. Miller Interviews. 9-16 January. 1976年約瑟夫·米勒訪談。 1月9日至16日
. 1977. Letter to Joseph T. Miller. 28 July. 1977年約瑟夫·米勒訪談。7月28日
. 1983. Peng Shuzhi xuanji. Volume 1. Hong Kong: October Bookshop. 1983 彭述之選集。 卷1,香港:十月書店
. 1984. Peng Shuzhi xuanji. Volume 2. Hong Kong: October Bookshop. 1984 彭述之選集。 卷2,香港:十月書店
. 2016. Peng Shuzhi huiyi lu. Volume 2. Hong Kong: Tiandi.
2016 彭述之回憶錄。 卷2,香港:天地圖書
Qiang Chonghua, Yang Shujuan, Wang Shudi and Li Xuewen. 1982. Chen Duxiu beipu ziliao huibian. Hunan: Renmin chubanshe. 強重華, 楊淑娟, 王樹棣, 李學文 編。1982年,陳獨秀被捕資料彙編。湖南:人民出版社
Saich, Tony. 1996. Edited.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New York: M.E. Sharpe. 中共力量的興起:文獻和分析。 紐約:M.E. Sharpe。
Schram, Stuart R. 1999. Edited.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ume V. New York: M.E. Sharpe. 毛澤東的權力之路:革命文集 1912-1949。 卷5。紐約:M.E. Sharpe.
Sheng, Michael M. 1997.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打擊西方帝國主義:毛澤東,斯大林和美國。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Sheng Yueh. 1971.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Lawrence: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個人記敘。羅倫斯:堪薩斯大學出版社
Shi Fan. 1932. ‘Zao yaoyan gaibianbuliao chichi ah!’ Huo Hua. Volume 1 Number 10. 石凡1932,‘造謠言改變不了事實啊!’火化,第一卷第10期。
Sin-Lin. 2012. Shattered Families, Broken Dreams.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Steven I. Levine. Portland: Merwin Asia. 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夢想。 由Steven I. Levine譯自俄文。 波特蘭:Merwin Asia
Socialist Appeal. 1938. ‘GPU Tries to Frame Chinese Bolsheviks’. Volume 2 Number 10. 5 March. 社會主義訴求,1938。“格別烏嘗試框住中國布爾什維克”。 第2卷第10期。3月5日。
. 1938. ‘Slanders Against Chen Tuhsiu Repudiated by Noted Chinese Scholars’. Volume 2 Number 22. 28 May. 1938年。“對陳獨秀的誣衊遭中國知名學者否認”。 第2卷第22期,5月28日
. 1938. ‘Chinese Trotskyists Lead Strike Against Japan Ship’. Volume 2 Number 36. 3 September. 1938年。“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打擊日本船隻”。 第2卷第36期,9月3日。
Stranahan, Patricia. 1998. Underground: 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27-1937.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地下活動:1927 - 1937年上海共產黨和生存政治。 紐約:Rowman和Littlefield 出版社。
Tuolouciji [Trotsky]. 1947. Zhongguo geming wenti.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Xiao Kechuan [Wang Fanxi]. Shanghai: Chunyan chubanshe. 托洛茨基。1947。中國革命問題。 由王凡西編譯。上海:春燕出版社。
Wakeman, Frederic, Jr. 1995.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年,警務上海,1927 - 1937年。 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
Wang F. [Wang Fanxi]. 1974. ‘Memoirs of a Chinese Trotskyist’. International. Volume 2 Number 3. 王凡西。1974年。“一個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回憶錄”。國際。 第2卷第3期。
Wang Fanxi. 1991. Memoirs o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regor Bent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王凡西。1991 年。“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憶錄”。由Gregor Benton 翻譯並作序。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Wang Jianmin. 1973. ‘Chen Duxiu via yu Zhang Shizhao chu ting’. Zhonghua yuebao. Part one July. Part two August. 王建民,1973。‘陳獨秀與章士釗出庭’。中華月報。第一部,7月,第二部,8月。
Wang M.Y. [Wang Fanxi]. 1948a. ‘China’s Trotskyism in the War: Was China’s War Progressive?’ The New International. Volume 14 Number 2. 王凡西,1948a. “戰爭中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中國的戰爭是進步的嗎?”新國際。第14卷第2期。
. ‘Problems of Chinese Trotskyism: Conclusion of the Minority’s Document’ New International Volume 14 Number 3. “中國托派主義問題:少數派文獻的結論”新國際,第14卷第3期。
Wuchanzhe. 1930. ‘Xiehui weiyuanhui zhuan ‘Women de hua’, ‘Shiyue she’, ‘Zhandou she’ quanti tongzhi’. Number 6. 無產者,1930.“協會委員會撰‘我們的話’,‘十月社’‘戰鬥社’全體同志”。第6期。
Zhang Kai. 1994. ‘Remove all false allegations on the Chinese Trotskyists’ Shiyue pinglun. Volume 24 Number 4. 張開,1994。 “消除所有對中國托派人士的虛假指控”。 十月評論,第24卷第4期。
. 2005. ‘Zhongguo Tuopai zai kangzhan zhongde zhuzhang he xingdong’ Shiyue pinglun. Volume 32 Numbers 2/3.
2005年,“中國托派在抗戰中的主張和行動”,十月評論,第32卷第2/3期。
. 2015. Joseph T. Miller Interview. Hong Kong. 10 November. 2015年,約瑟夫·米勒採訪。 香港。 11月10日。
Zheng Chaolin. 1980. ‘Chen Duxiu and the Trotskyists’. in Benton. 1996. 鄭超麟, 1980。“陳獨秀和托洛茨基主義者”。 本頓,1996年。
. 1997. An Oppositionist for Life: Memoir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Zheng Chaoli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regor Benton.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畢生反對派:中國革命家鄭超麟回憶。 由Gregor Benton編譯。 新澤西:人文出版社。
Zheng Xuejia. 1976. Suowei ‘Tuofei Hanjian’shijian. Taibei: Guoji gongdang wenti yanjiu. 鄭學稼,1976。所謂“托匪漢奸”事件。臺北:國際共黨問題研究。
. 1989. Chen Duxiu zhuan. Volume 2. Taibei: Shibao wenhua. 1989年,陳獨秀傳,卷2,臺北:時報文化。
[1] 約瑟夫·T·米(Joseph T. Miller):伊利諾斯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退休兼職政治學助理教授,電子郵件:[email protected].
[2] 關於中國托洛茨基主義一般背景的英文介紹見:卡根(Kagan),1969年;米勒(Miller),1979年;本頓(Benton),1996年;和本頓(Benton),2015年。“中國左派反對派”和“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這個術語經常互換使用。
[3] 該組織的創始文件“我們的政治意見書”(Women de zhengzhi yijian shu)全文見: Peng,1983:305-35。五個部分中的三個被翻譯成英文,1996:414-28
[4] 有關統一會議事實真相的爭議持續了多年。
[5] 據王說,改名發生於1936年初。陳碧蘭(Chen Bilan)寫道,從1931年起,統一組織取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見 Wang, 1991: 173-4;陳,1980:32;Glass,1990 [1939]
[6] 在中國的這些有限成功出現的當時,身處蘇聯的中國反對派活動分子正遭到劇烈攻擊。 1931年5月至7月,“十九人案件”在莫斯科進行審判,導致許多人被監禁。 參見 Sin-Lin,2012:295-8。
[7] 這一重要事件的範圍,正如作者的介紹,‘中國長期內戰突然陷入中日之間的區域性戰爭,所以當1941年衝突成為全球性的時候,中國人進行的內戰處在區域戰爭中,這個區域則處在一場總體的全球戰爭中。’ Paine,2014:5
[8] 1932年2月29日,關東軍在瀋陽召開會議,討論滿洲未來。 它單方面將其名字改為滿洲,但是在國際上滿洲國的音譯更為出名’ Paine,2014: 17。
[9] 陳其昌在1943年被日本警方逮捕、磨和處決。彭述之對陳其昌的批評,見 Peng, 2016:358-61。
[10] 與中共決裂之後,以撒把印刷社和印刷鉛字捐給了共產主義同盟。 然後他去了北京,開始研究‘中國革命悲劇’的原因。 Hirson,2003:127-8; Isaacs,1985:28-32
[11] 關於托洛茨基對“民眾陣線”與“統一戰線”的評論,見 Evans and Block,1976:594-6。
[12] 有關此期間的“綏靖者和叛徒”的最近討論,見Coble, 2015: 75-9。
[13] 應該注意的是,劉家良很快就轉而反對王的立場。
[14] 此文最初發表在‘保衛馬克思主義’叢書,該系列出版了許多發生在1941年至1945年期間的同盟裡的辯論文件。
[15] 王凡西指出,雖然採取彭的立場者原來是少數,但該立場曾經成了第四國際的主要路線,通過了其自己關於戰爭的決議。 見Wang,1991:234-5。
[16] 關於應用在國際托洛茨基運動中的“革命失敗主義”概念,有非常有用的歷史回顧和分析,見Joubert,1988:1:3
[17] 另外,見“關於戰爭的決議”,“Evans and Block”, 1976,574-7.
[18] 關於第四國際內部爭論的材料彙集,見 Matgamna,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