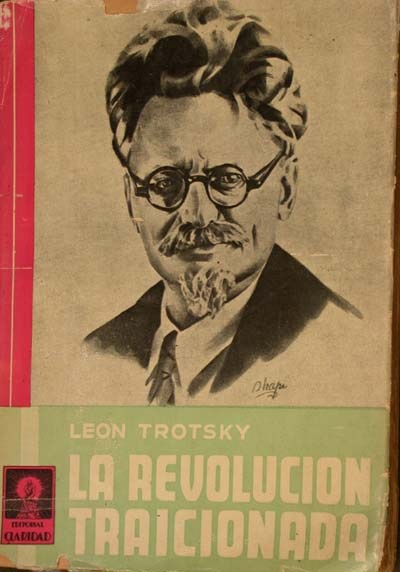
訪托洛茨基談俄國問題
1938年3月25日
托洛茨基:就蘇聯的社會關係的演變的具體形態和新的狀況作論述,真可是難乎其難,因為近年的資料和統計數字較之以往愈發是捏造和虛構出來的東西。報章方面也如法庭一樣,絕對是堆砌營造出來的東西。就有關於蘇聯的社會陣營方面,報章上的東西是絕對的虛假。 最上一次做的人口普查給下令銷毀;我不知道這則新聞是否有傳到美國的報章去;這可是一宗至關重大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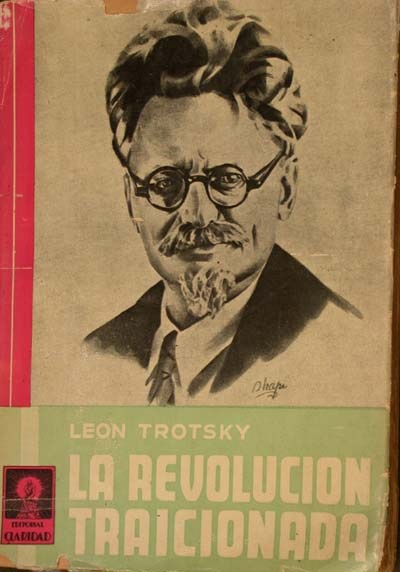
我在《被背叛的革命》裡,批評官方的統計數字和資料懷有著這個目的,就是用以掩飾社會的層級化,掩飾官僚和工人,農業工人和集體農莊的經理的薪酬差異,以及家庭僕人的數量。我估計在集體農莊方面有不下於5百萬戶家庭和官僚貴族擁有家僕,而在城市裡,[每個家庭的]家僕人數甚至有2個,3個或以上,當中包括了司機和看管兒童的保姆。這是一個僕人的社會階級,專為高上階級服務,但這一切並沒有收進人口統計調查的報告裡。
這個人口普查是在1月進行的;接著,全世界得知官方頒佈了一項特別法令,以把這個人口普查的資料燒毀,因為那些統計數字是由“派托分子,捏造家,人民之敵”等人搞出來的。至於那個至為基本的,用以衡量蘇聯的狀況的最為重要的東西——人口的規模——也沒有予以發表。華爾特·克裡維茨基對此在法國報章上作了充分的解釋,而米柳科夫的報章也刊載了這則解釋。人口是非常大幅度地下降了。每年的人口增長是3百萬人。
沙克曼:上一次的人口普查是何時做的?
托洛茨基:是在1920年代,當時也顯示出相當的人口增加;那時的人口估計約有1.17—1.18億人。可是克裡維茨基聲稱,去年普查的人口只有1.3億人。這個結果完全是場浩劫,因為它是對人民生活條件的最佳測驗。這個數字顯示出,在1931 —1932年,因集體化,流放,成千上萬被暗殺的農民以至因饑荒而損失的人口是數以百萬計。我相信這並且只是事實的一面。它還顯示出人民在平常時期的生活條件是非常的惡劣,死亡率是非常的高,人口的年增長並非以三百萬而卻是1百萬計——這就是五年計劃所宣稱的整個“高度幸福繁榮”的時期的結帳。
我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引用的資料是來自謝多夫為我保存的地方報章內的資料;這些資料讓砌出局部的真相成為可能。自此以後,便再難從報章裡找到任何稍微貼近現實的東西了。我在米柳科夫在巴黎出版的報章上找到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是對一個半托洛茨基分子的訪問錄;這個人的名字沒有發表,但我估計那人就是克裡維茨基——他這個人傾向于資產階級民主。據受訪者表示,農民的形勢有了改善,但工人的形勢是非常惡劣;國民收入的差異性是有步驟地對農民有利,對工人不利。假如我們所說的農民是集體農莊的貴族的話,這種狀況會是真實的——行政人員的形勢是近乎老闆的局面,是個商人,因為集體農莊農民有權在市場買入和賣出至少一部分物質。行政人員兼是半官吏和半老闆。他的收入非常大,他並且同時也是格柏烏(秘密員警)的代表。人們可以想像到,像這樣的一個行政人員手上集中有多少權力。至於農場工人或工廠工人的局面則是迥然不同;經濟力量的關係是朝向有利於較高的階層即集體農民而變化的。這種形勢標示了社會的社會分層化之惡化。同時並進的是官僚把經濟權力集中到它自己掌上。
莫斯科大審判就是這個過程的表達之一;各種政治矛盾自然的反映著社會的狀況。官僚對人民無比畏懼——它對人民之憎恨,還甚于沙皇——這是由於人民具有兩次革命的傳統,並且不完全是目不識丁。在人民之間也有著互相敵對和互相摩擦。尤為重要的是官僚內部之間的互相敵對;審判就是這種敵對的直接表達:一部分的官僚消滅另一部分的官僚。
沙克曼:為什麼?
托洛茨基:這是由於群眾的不滿甚至乎也令致官僚體內部產生了不同的流派。一部分官僚說:“讓我們作出一些讓步吧。”而另一些則是反對。群眾的壓力令統治層產生分裂,這就和世界各地相同。
很難說官僚的政治分歧是什麼,不過莫斯科的大審訊為此給予了很好的提示。其中有些人是希望恢復資本主義,而另有一些人則是反對。[審訊上的]指控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
另一項事件的規模雖然小,但是極其具有啟發性,為我們提示了分歧的所在,那就是和莫斯科決裂的人。在這方面我們有賴斯,在希臘的代表巴爾文,在德國的軍事情報主腦克裡維茨基——這些人中,只有4到5人具有如克裡維茨基的重要性——及從羅馬尼亞逃往義大利的布堅科。我們知道在過去數年裡,外交部人員被選換和清算的不下十次,我們也知道有多少人被召回及謀殺;不過,繼大清算之後有4個人是逃出生天了。這是個十分高的比率,它表明了官僚體內的離心力是非常的巨大。這些人不是我們偶然在街上碰到的最先4個人哩:當中一人是希臘的部長,另一個是在德國主理秘密事務的頭子,而賴斯和克裡維茨基屬於同一級別,具有幾乎相同的重要性。而這些人走到什麼方向呢:萊斯立即宣佈效忠第四國際;巴爾文保持友好;克裡維茨基面向資產階級民主(他是個自由派,和孟什維克有關係——他與我們斷絕聯繫,這尤其在我們的兒子死後更甚,而這點不過是他的口實而已);布堅科成為了法西斯分子。不過是區區4人,但極具有代表性——這是體現出官僚體系內部各種政治色彩的一道彩虹。它說明了斯大林為什麼會從黨機器過渡到格柏烏去。現在的政治局不是政治局,而卻是斯大林-葉若夫。審訊上隨便一個被告可以點名政治局中人,而那個人就會受到審訊——我們在魯祖塔克身上可以看到這個例證:他曾經是政治局的候選人,而我肯定並無點名這個人;給他點名的是葉若夫。
在此有一個對我們十分重要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受到俄國白衛隊廣為討論:在俄國政府裡有沒有托洛茨基主義者?甚至連維克多·塞爾日也確證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數量誇大得驚人;而斯大林這麼做是有理由的。據來自俄國的人確證,在蘇聯有的只是右翼傾向——沒有左的傾向——至於托洛茨基主義只不過是個幻影。這既真實也不真實。在官僚體內部,右的傾向與時俱增,甚至走向成為法西斯。在群眾裡的社會基礎不相同。要是我們抽出個別一個年輕的官僚分子——這個人會是一個全然的法西斯類型:他沒有十月革命的傳統。他有的只是備受紀律:備受發槍彈的紀律,備受清算的紀律,及備受經受審訊的紀律——而這一切全是為了祖國的光榮。在官僚分子當中像布堅科這種人格非常重要。像賴斯同志之類的比率非常之低。在群眾中的各種傾向是要較為初級的,但都是朝向于反對官僚,反對新的貴族;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們並不是真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但他們的態度和總的批評本質是不謀而合。只不過于極權政體的障礙使然而無從建立起聯繫而已。
我們在西班牙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相同的事情。1936年7月工人大眾的行動發展絕對是朝著我們的方向邁進的,可是我們的同志的數量十分之少,其數量少的程度使得那個被稱為派托的POUM組織對於群眾間的動勢之反映甚少,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我們受到可怕的仇恨。
我相信,個人恐怖主義在俄國是勢無可免的了。他們的審訊激發了恐怖主義,就像沙皇當年。成千上萬宗槍決裡竟然沒有其中一人的兄弟姐妹,把那麼一個官僚槍殺是不可想像的。官僚盡其可能的廢棄馬克思主義反對恐怖主義的傳統;個人走向恐怖主義的傾向是由審判繁殖開來的。他們將要獲得的收成,是由他們用個人恐怖主義的形式撒播的種子而來。由於群眾運動沒有一個黨,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外省各地,恐怖主義的行為數不勝數。謀殺基洛夫的尼古拉耶夫其人的人格不為人知——或許其中的原因甚是一般,比如涉及女人。國外格柏烏情報局頭子斯盧茨基被克裡維茨基問及尼古拉耶夫行刺的原因時,斯盧茨基對他說:“不要問,那太莫測高深了,最好是不要問。” 斯盧茨基接著告訴克裡維茨基,斯大林前往列寧格勒主持這宗暗殺案件的初訊,以便為調查的方向發給指示。
沙克曼:我們之間也多次討論這點:斯大林在前一段時期為什麼不曾被暗殺呢?
托洛茨基:有兩個理由:(1)誠實而又嚴肅的人士並不相信這種行動會達致任何成果;他們會說:“那又由誰來取代他呢?莫洛托夫嗎?難道莫洛托夫會比斯大林好些嗎?” (2)斯大林本人左右護衛森嚴。歷代沙皇中也無一人比他有著更森嚴的護衛。不過,儘管如此,由於從下和從上而來的壓力是如此的利害,致使接著而來的時期必定會興起恐怖主義的狂飆。這類行動能否令事情發生基本的變化,這點是大成疑問的;他們能夠令推翻斯大林集團的勢態加劇,但是較為有意識地贊同資產階級的分子也不曾做好準備。至於在革命分子方面,我們不能期望他們會利用這種行動所帶來的機會,就像我們在反對沙皇的鬥爭中所做到的一樣。我們反對社會革命黨人的方法;但在每次發生恐怖主義行動之後,我們會宣佈我們同情社會革命黨人,把理由交待,並且把反對沙皇的情緒動員起來。而在目前,我們沒有能夠做到這種宣傳的組織。
戰爭在初期時必然會強化斯大林的地位:官僚和人民因自保的精神而將給予克里姆林宮一夥予新的氣象。但到了戰爭期間,事情就會如其他國家一樣的了。政權解體,而戰爭將會標示出政權必然的死亡。政權將由什麼來取代,這是一個總括性的問題的其中一個部分。假如戰爭在資本主義國家造就了一場革命,則斯大林集團一夥的倒臺將不過是戰爭裡一段次要的插曲——假設它的倒臺沒有即時的由工人組織(蘇維埃)所取代的話。我們若是有那麼一刻間接受這項假設,即這場戰爭將標示我們文明的終結,則俄國自然是將要亡國。但這個假設的可能性很低。我們寫道,斯大林的垂死掙扎——而這並非誇大之詞——同時也標示著共產國際的死亡。共產國際將會在蘇聯克里姆林宮一夥肯定地垮臺之前結束它之作為一個生機蓬勃的運動,這點不僅有可能發生,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是多半會發生。不過,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端賴於我們本身的政策。
共產國際是什麼?它有3道支流:(1)其機關,它由惡棍和見識淺狹的狂徒構成;(2)在這種時期被吸引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3)工人;其中主要的一大部分人早在這階段之前已為黨吸引過來。前兩道支流——即來自機關和知識份子的部分——有可能投向洛夫斯通分子方面去(他們要投向我們是難乎其難的;而我們希望,我們對機關分子和知識份子不要太客氣——我只能重申,我們必須設立嚴肅的規則對待他們,至少須維持1年的察看期)。
至於第3道支流方面,即是斯大林黨內的工人,他們並非機關人員,而只是基層成員。這類工人倘若留在黨內到現在,那並非由於他支持莫斯科的審判,而是由於工人有著非常深刻的獻身精神和感激情緒,在心理方面更為穩定。無論發生什麼事,他仍然留在黨。他的謙遜使他會說不明白所發生的事情。知識份子可能會比工人先脫離黨。但工人一旦和黨決裂,他們會趕緊加入我們這一邊來,而非到洛夫斯通分子那一邊。
正因為如此,在斯大林黨內有一個核心小組以向一些分子進行解釋,準備及收集訊息是重要的。我相信我們現在並無這類訊息;而設立參謀部以在斯大林黨內和斯大林主義者作鬥爭是必須的,而這個鬥爭自然的是在我們的黨的領導下。由一些青年同志首先收集訊息,從以下的角度研究整份斯大林主義報章:黨內出現了什麼事情,發生了什麼衝突,逐出黨的事件等等。然後是在黨內有直接的情報員,而這是在良好意義上的情報員。我相信,在他們的辦事處人員之間,在技術人員和顯赫的領導之間的分化必定是非常尖銳的。白勞德是斯大林的滑稽版——技術事務是由絕對無足輕重的人組成的。我們可以首先從清潔工這一類人士入手吧。打字員吧。有些打字員是為白勞德,為格柏烏服務,是擁有特權的打字員;但另有一些人他們完全是從事於技術性的工作,完全為人所忽略。我們必須從這些方面找得我們的情報員,有系統地找出這些人,滲透進去,尋根究底,與共產主義工人進行友善的交往,逐點逐滴地創造出一個訊息網路。
卡農:你會找哪一類型的同志主理這種工作?負責這類工作的同志該擁有什麼特點?
托洛茨基:像阿本這樣的同志是適合的。我不曾會晤過他,也不認識他;但我就是有這個印象。這個同志要能做有系統的工作,必須有年輕的合作者,有獻身精神的女性也能勝任,但必須是聰明的女性。她們自有其他方法以與共產主義工人分子取得聯繫。
沙克曼:你是指派人進入共產黨嗎?
托洛茨基:是的,若是可能的話。你們是知道法國的例子。俄國青年加入到社會主義青年去,目的是把後者爭取過來。他們舉行了秘密會議,但佛裡特·澤勒秘書是我們的同志。我們與她討論了這件事,請她立刻把記錄刊出。我們把會議記錄刊出後,贏得了所有青年人。澤勒仍有疑慮,但基層立即對我們深表同情,那麼澤勒便隨他們一道投向我們了。
卡農:記錄是在未獲授權下刊出的嗎?
托洛茨基:當然囉。澤勒後來說:“我的秘書比我更聰明。”在反對斯大林派的鬥爭中,戰爭問題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勒德洛修正案非常重要,是個試金石。這個修正案誠然並不足夠。即使斯大林派贊成勒德洛修正案,這個修正案的重要性更10倍於此。我們最先對待這個修正案的態度,是有點兒教條和宗派性;但最佳的做法是公開地宣佈我們已經改變了路線。實事求是地說出來是最好的。你們可以說我們改變了綱領,並且舉出列寧在農業問題上的改變為例子。我們對工人並不玩弄把戲。我們提倡更為革命性的鬥爭,但我們仍然是個微小的少數派。你們相信勒德洛修正案之作為對大商家和政府的牽制;我們會隨著你們一起走。但全國委員會最近通過的決議案以及麥金尼說我們並沒有作任何改變的聲明卻是不真實,不坦誠的。人們不能做出轉向而又不將之告訴大眾——要是這樣的話,就是沒有轉向了。我們必須說:“是的,我們做出了這個轉向,因為我們希望和你們共進退。”這麼強調地說出來,以至連洛夫斯通分子也沒膽敢來指責你了。而洛夫斯通分子是無足輕重的。這關係到我們與工人階級的關係——這才是舉足輕重之處。
[以下討論,論及到勒德洛修正案假如經過修訂,沖淡後再度提交到大會討論,我們該採取什麼立場。托洛茨基說,他需要在看到新修訂的議案後才能發表意見,但不管如何,我們現在便應該為既有的修正案作鼓動,並且指出原提議人刻下也沒有能力為之鬥爭了。]
沙克曼:你把支持勒德洛修正案一事和支持解除軍備一事兩者區別開來嗎?
托洛茨基:解除軍備絕對是另一回事。這個提法是絕對錯誤的,完全是無中生有。勒德洛修正案則迥然不同,工人希望制衡政府,而這與國際聯盟,仲裁法庭及談論解除軍備無關。我提議我們把修正案青年人年屆18歲須享有投票權的要求兩者聯繫起來。
鄧尼: 當戰爭屆臨時,18歲的男孩就會是21歲的了。
托洛茨基:對,對,這是另一個論點。
卡農:你認為斯大林派運動在美國有任何發展前景嗎——會進一步擴張嗎?過去數年來,他們不僅在數量方面大增特增,而且影響面也很廣泛。我會認為他們在美國的影響力已經達到頂點,除非是由於戰爭使然,他們得到政府的允許而作為職業愛國者和無所不能的員警人員以對付我們。總的來說,莫斯科審判所得到的可怕反響,人民陣線政策及他們的外交政策方面普遍的破產,在在都給美國的斯大林主義運動帶來沉重的打擊。現時在美國,反對斯大林主義的來源是較為廣泛的了。就在他們控制過的許多工會,也有強大的反對派發展起來。我們的同志對我們說,仇視斯大林的情緒正與日俱增,例如在斯大林派和最不堪的匪幫分子混成一體的油漆匠工會,就有這種情況。
沙克曼:此外,也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症候。紐約有兩份自由派報紙:《世界電訊》和《晚報》,是由強烈擁戴羅斯福的斯特恩任編輯。可是直到昨天,尤其《晚報》卻對斯大林十分包容,非常友好。
托洛茨基:我讀到梅耶和編輯之間就俄國問題發生的爭執;這很有意思。
沙克曼:是的。現在《晚報》展開了反對莫斯科審訊的運動。至於《世界電訊》則刊登了施托爾貝格的文章,這傷害了工會內的斯大林派。
托洛茨基:我相信西班牙來臨中的失敗——西班牙政府在未來數周內將會潰敗——將會產生浩大的反應,而這將會指向斯大林派,反對他們。失敗之後,每個組成部分將會互相指責。來自西班牙社會主義者的仇恨很是深重,而志願人士即將復員歸來,那時我們便會有數以百計的貝蒂了,因為內戰是一所偉大的學校。接著就是法國的人民陣線,完全是一敗塗地。今日的電訊顯示,美國的股票交易所又再度神經兮兮,下跌了。這標示了新政及其所有幻想最後的一次痙攣。這二個因素——西班牙的失敗,法國人民陣線的失敗,以及,容許我說,新政的失敗——標示著對民主黨人的致命一擊。這自然也視乎於我們方面的行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第二國際似乎完全死亡,而第三國際在初期的年月裡發展不斷。我希望現在……。
卡爾斯納:當時有勝利,所以第三國際有發展。但工人現在不論放眼何處,到處都是失敗。工人不僅對斯大林主義幻滅,並且也對共產主義幻滅。我懷疑那些從西班牙回來的數以百計的人會是加入我們哩,或是離開運動。
托洛茨基:這絕對正確。它給予我們高度困難。在不同的時期內,我們所選取的幹部也有所不同。那時的幹部追隨勝利的國家,現在他們追隨的只是個革命的綱領;我們的發展比起共產國際是更為緩慢許多。另一方面,我們會有新生的一代;我們必須不能忘記,新的一代沒有經歷過斯大林主義者。我們的整個問題是要為我們的幹部和工人之間找出聯繫。年輕的一代並不精疲力竭,沒有疲倦下來,此所以我們爭取到共產黨內的年輕人,而共產主義青年開始轉向我們,這是有代表性的。這是朝向我們的首次重要的動勢;我們將會增長。
(《托洛茨基文集1937-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