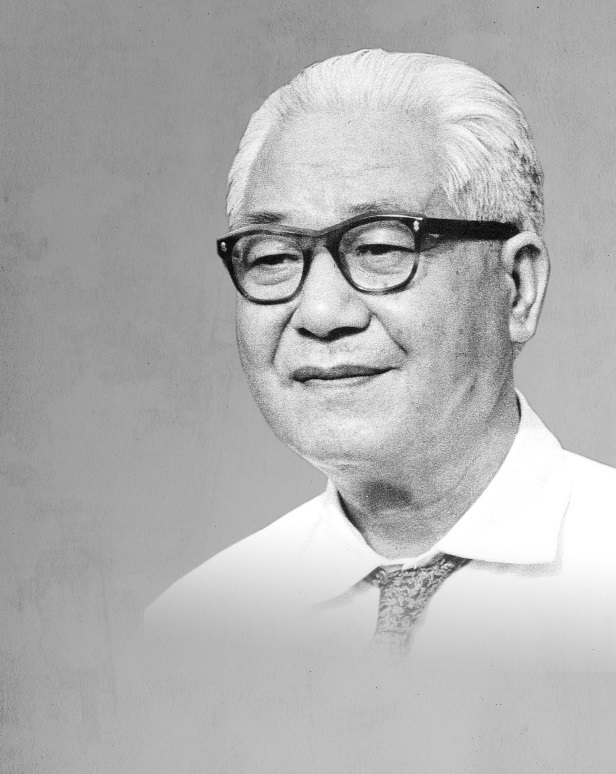
彭述之:我的一生經歷憶述 (二)
( 訪問者: 鄭致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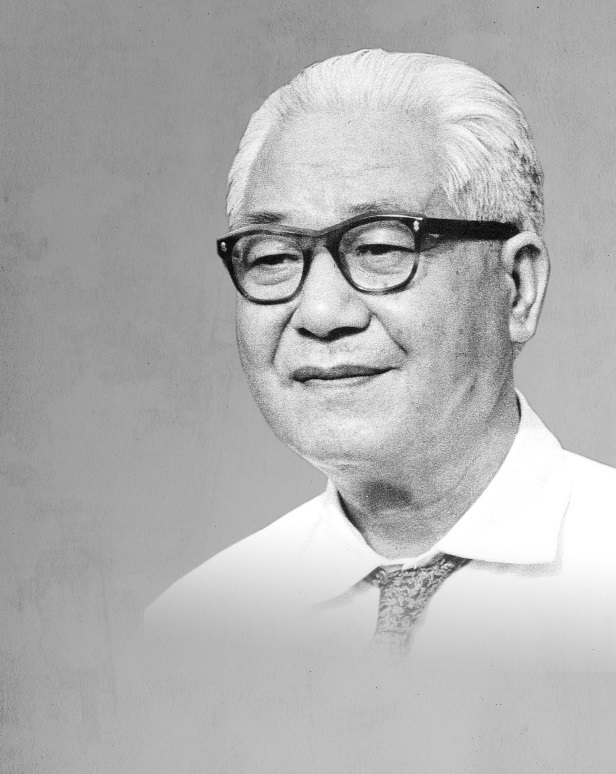
(八) 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
這是我親身經歷,也感覺很深刻的。人們對革命的熱心冷下來了。由此可以知道後來蘇聯的官僚主義為什麼抬頭,托洛茨基那個反對派為什麼支持的人不多。因為對世界革命十分失望。
1923年11月7日開始的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運動,是由《真理報》一篇文章引發的。
在這以前,托洛茨基的意見,尤其是關於工業化是跟斯大林不同的。托洛茨基在1923年初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剪刀差,就是城市與鄉村的問題、工業與農業的問題。托洛茨基跟斯大林之間最大分歧,到了1923年11月開始,就爆發出來,非常的激烈。因為我同時是蘇共黨員,那時也懂俄文了,所以,我以俄國共產黨黨員的資格,同時是中國支部的負責人,所以我有權責去參加各種爭論會。那時俄國還沒有像後來那樣,黨內提出的不同意見還是可以討論的。甚至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提出的一系列意見,關於工業問題、農業問題,有一些是關於黨的民主問題,尤其是後一問題,爭論得非常激烈,在某些場合簡直打起上來。在那時候、那種情形,我的感覺是為什麼會這樣子?我們還不完全瞭解內幕,就我個人說,因為有許多事情,從前都是掩藏,不讓一般黨員知道的,只有上層少數人知道。所以,我們就感覺到這種情形,俄國人不同,尤其是年輕的人更激動。那時我們感覺到的一個問題,特別是關於老人的,所謂保守派的問題。另方面,我們對托洛茨基的一種崇拜,我們從中國到莫斯科的,腦海只認識列寧和托洛茨基二人。看文章也是看他們的,到了俄國就更是如此。無論什麼地方,掛的照片都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後來我們知道他們的意見,知道他們在革命中的貢獻,當然對他們有更深刻的認識了。所以,對托洛茨基、列寧是一樣的,對斯大林的印象不好。社會上,對他認識不深。尤其是我聽他的演說,都要打瞌睡的。聽托洛茨基演說就興奮得很。這是年青人的一種印象。
對於他們的鬥爭,我們覺得斯大林不對,但是還不能夠辨別。很難,很不容易。比如老人跟青年,這些老人都是在過去十幾二十年幹革命,崇老,所以我們對老革命家都很尊重。但同時看到年輕人很活躍,精神很好。所以,這個問題,年青人就很難瞭解。托洛茨基那本《新路線》,我也看了。他說,老的人會墮落,在那時候看,很難懂。當然後來懂了。那時候,我們對這些,也沒有擬好一個綱領。別人也不能幫助我們。我覺得這種情形不是很好,要研究為什麼會這樣?關於托洛茨基的意見,關於農民的剪刀差,我是完全同意的。不過老的人要腐化,變成反動,這對我是個新鮮問題。不能夠瞭解和太難瞭解。當然,現在瞭解了。
1924年1月列寧逝世,這對俄國是很大一個衝擊。因為列寧的死,這個反對派的爭論就停止了。從那時候,斯大林對付托洛茨基的各種各樣壓迫手段開始了,由這件事可以看出來。第五次代表大會,1924年6月到7月召開,托洛茨基沒在大會上演說,沒有說話。大會上討論最激烈的問題是德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托洛茨基跟季諾維也夫、斯大林有很大的分歧。但會上並不公開說,所以與會代表不能瞭解這個問題。因斯大林一個人演說,托洛茨基沒有演說,就可以看出,我們已經感覺到托洛茨基受壓迫。討論德國問題最重要的是路特·費舍爾,一個女的,那是他們所謂的左派。就我看出來,當時我們感覺到的,他們這幫人支持斯大林。因為布蘭德萊總書記也被撤,當作一個代罪羔羊。所以這次會議沒有把德國1923年失敗的責任弄清楚 。就是斯大林一貫的做法,他失敗了,他不去好好弄清楚那個失敗的教訓。
至於中國問題、東方問題,我感覺到他們不願意講。東方的委員會由布哈林率領,我們有中國的代表四人,就是李大釗、彭述之等。我對這次大會沒有感覺得到什麼東西。不過那時候中共中央要我回國工作。
現在要談一般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發展,從托洛茨基主義開始到現在的情形,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和政治主張。
(九) 回國組織左派反對派
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中國,主要是由於中國革命的失敗,少數的人像陳獨秀和我覺得這失敗完全是由於共產國際的政策錯誤。我們檢討教訓,還沒有看到托洛茨基主義和托洛茨基的文件,我們已經根據自己的經驗,已經反對共產國際的政策了。例如,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斯大林跟布哈林把反對的對方打壓住,我們就覺得,這個共產國際沒有希望,不能改變,所以我們拒絕開會,就可以看出我們的態度。隨後看到托洛茨基的兩個重要文件:一是關於整個中國革命運動的理論,過去政策的基本錯誤,這個文件就是中國革命的總政策。另一個是第六次大會以後,有一個中國的革命問題。當時要提供一條路線,以代替斯大林的那種冒險主義,就是在反革命時代採行的政策問題。我和陳獨秀看了這兩個文件,我們沒有猶疑就認同托洛茨基所說的,無論對過去對未來都是對的。所以決定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組織一個左派反對派。1929年4月間,那時另外還有一個小組織,就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一批中山大學學生。他們已經開始組織托派,但是,這批學生有個嚴重的缺點,這批學生從前在革命之中,沒有人做過負責任工作和領導的,在1925年孫中山大學開辦以後,才把他們送到莫斯科。他們沒有革命經驗,直接從托洛茨基的文件吸收和認識,從托派思想的拉迪克校長處受到影響,所以贊成托洛茨基思想。他們回來後,在黨內沒有地位和不能到黨工作。就在外找少數的人組織一個團體,出版《我們的話》。這樣的組織沒有影響力,尤其在黨內沒人知道。在外也沒人知道,所以我們也不知道,那時我們還在黨內的,就可見他們沒有影響力。到了我們組織左派反對派時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一方面,像陳獨秀和我組織反對派是在過去黨內擔當最高責任的領袖,黨員差不多全是幹部,他們當中有省委書記、中央委員。上海有批工人,曾參加黨和幹部組織起來的五卅運動的。像這樣一個左派反對派在世界上是第一個,在當時社會上的規模大和人數眾多,是最高的領導層。像美國是有加農,沙赫特曼,阿伯恩,他們曾是中央委員,但他們人數少,且從地位上來說,他們在黨內沒我們那樣高層的地位,在社會上沒我們那麼大影響力,陳獨秀、彭述之在革命世界中沒人不認識。領導上千萬工人運動,社會影響力是不同的。我們第一次簽名的,就是我們的意見書,我們共有81個人,81人都是黨的幹部,像陳碧蘭,她是上海區委的委員,也是婦女運動的領袖。所以組織了左派反對派,使整個黨都震動,全中國社會上都認為是大事件,共產黨分裂了。像中國著名的胡適之、大學教授們都發表了意見,我們的宣言公佈後,上海《每日新聞》日本報章翻譯了。日本寫的中國歷史還提到此事。新聞發佈後,中共翻譯俄文和其它文字,如法文、德文等。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內----第三國際,我們建立反對派,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關注。開始就呈現出與以前完全的不同。至於後來《我們的話》分裂成兩派。一派是王凡西和劉仁靜,他們另出版一小刊物沒有影響力。他們在黨內也沒影響。最後他們離開黨,沒有在黨內去影響群眾。我們使整個黨震動了。我們的組織是左派反對派《無產者》,《無產者》出版《我們的話》和《十月》刊物,從《我們的話》分裂出來的劉仁靜辦《十月》。 另外還有幾個從莫斯科回來。很少人想加入我們。他們不是很好的革命家,加入我們行列還提出條件,劉淵要做中央委員。組織還沒成立,談什麼中央委員?他們另外成立組織和出版《戰鬥》小刊物。我們主要是在黨內爭取幹部、黨內革命分子。宣言發表後,引致黨內震動,三個組織召集聯席會議,中央、江蘇省委、地方組織和我談話。準備開除我們。不過沒莫斯科命令,他們不敢單獨開除的,一定要得到莫斯科的允許。後來莫斯科的命令開除我們,因莫斯科最怕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主義是根據地方的關係,地區、省份和個人的,我們在黨內領導革命運動多年,有成千幹部和我們接觸。革命失敗後,很多幹部還留在黨工作,他們跟我們有接觸,所以接受托洛茨基思想,組織左派反對派。因我在黨內同幹部接觸最多,陳獨秀比較少,我常到各地,上海區經常出席上海區委的會,每星期一次,和每星期出席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我常作報告。上海有上百名活動分子和我接觸最廣泛。在莫斯科幾年,當時的幹部和學生,後來在黨內都變成幹部領袖,我和他們關係密切。開始,我和一些老幹部接觸,跟他們談托洛茨基的意見,談過去革命失敗的教訓。一兩個月後,開始組織了幾個約三四十人的小組。我們集結起來,成立一個正式組織,反對派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包括陳獨秀、尹寬和我。所有成員分成小組還在黨內部工作,在黨內也有小組,小組有鬥爭,說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說黨的政策不對,批判各種機會主義鬥爭。還在黨內的幹部,還不知道托洛茨基主義思想組織的人,我們都接觸了。陳碧蘭在中學教書,她接觸一批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這些人都在黨內擔任重要的工作,由於她接觸了,所以又有一批人加入了托派,加入反對派。組織就擴大了,因此,我們辦了《無產者》刊物。送給黨內人看,當然外間人也看,這是秘密的,因在國民黨統治底下不能公開。
隨後,我們出版了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問題,除了那最初看到的兩篇文外,又找到更多文章,出版一部書送給黨內人看,對社會的影響更大,我們自己的組織生活正式開始。
1929年3、4月至12月,黨內要開除我們。陳獨秀寫了政治意見書。我也寫了政治意見書。尹寬也寫了,還有其他的同志。他們組織特別的批判會批判我們。12月陳獨秀寫了最著名的《告中共黨員書》。陳的檔案還保存著,我的就失去了,因我幾乎被捕,所有文件都丟掉。後來我們合寫《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是正式宣言----81人宣言,事實是三人合寫的,陳獨秀、尹寬和我。這是所有托洛茨基派,蘇聯以外的一個最有系統的文件、最詳細的文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樣的文件,德國、蘇聯都沒有。我們是有系統的攻擊斯大林的共產國際、攻擊斯大林的思想和主義、官僚主義。這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一個基礎,應該從這開始,因為很有系統。托派的中心思想是《不斷革命論》,斯大林主義是一種階段論,違反了不斷革命論,就是我們理論上比較最高的理論基礎。
1930年夏天,開始形成一些小組織。事實上除了《我們的話》在工人有地區關係如香港。上海有少數的人是黨外的,都是莫斯科回來的,他們也有他們的委員會和組織,不過他們沒有影響力,除了香港有少數的工人,一二工廠或船務工廠沒有多大的影響。北京有些學生後來分裂了成兩部分,這兩部分又互相鬥爭,最攻擊的是《無產者》。尤其是《十月》社的劉仁靜和王凡西說,陳獨秀是過去的機會主義者,執行了機會主義路線,寫了文章攻擊陳獨秀。後來托洛茨基說:“你們應該好好向陳獨秀學習”。陳獨秀做反對派是執行斯大林路線的一個歷史重要事件,整個共產國際內部都很重視。陳獨秀在共產國際內外是第一號人物,因為中國有個大革命,中國的黨最大。從前一個黨的領袖,加入托洛茨基運動是最偉大的一件事,證明托洛茨基思想是很有力量的,這班人說陳獨秀是機會主義,這個機會主義不是陳獨秀,而是斯大林,陳獨秀只是執行者。他是沒有辦法和必須執行,後來托洛茨基告訴他們,參加我們托派運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們應跟他學習。所以,托洛茨基說這個爭論,這個攻擊《無產者》是被黨的領導利用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斯大林主義者利用了,在他們的幹部中說:你看,托派內某些人說陳獨秀是機會主義者,去宣傳,去蒙蔽他們的幹部。所以有許多老幹部不滿黨和不滿國際的鬥爭,像胡夢雄,羅章龍等,以前是在我們領導下工作的,我們的態度是沒有官僚主義的,後來瞿秋白和李立三完全是官僚主義的,對黨員壓迫得很厲害,不能說話,不能批評。所以,覺得陳獨秀和彭述之現在組織托派是有一定道理,表示同情並參考了我們的文章後,更覺有道理,包括劉少奇等。他們稱自己‘調和派’。但是托派內另一小組織攻擊我們,黨的領導拿去宣傳,調和派便失望,給托派很大的打擊,他們寫信給托洛茨基,攻擊「無產者」、攻擊陳獨秀派。所以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寫一封正式信給他們,說你們應該統一起來的。同時,我們的中文宣言《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翻譯成了俄文,寄給了托洛茨基。當時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對他們說,政治意見書跟托氏的意見是一樣,所以你們要跟他們統一起來。由於托洛茨基這樣說,這些人才放棄了他們反對「無產者」社和反對我們,才能統一。浪費了時間,同時放棄了很好的一個機會──在黨內影響所謂‘調和派’。在統一當中,最壞是王凡西的一個陰謀。他想利用這個統一操縱將來的領導機關,他幹了許多壞事情,陳碧蘭的回憶録都批評了和鬥爭過。
(十)統一大會後的工作和被鎮壓
1931年5月開統一大會。我對統一的態度有點不同意見,統一是應該的,是托洛茨基主張的。如果不詳細討論政治和組織問題,將來又要分裂,所以我的主張跟陳獨秀有點不同。我主張有一個時間討論政治和組織問題,有了基礎才統一。不過大家要統一,我不反對。所以,王凡西後來說我是反對統一的,這話不對。因這統一並不是經過認真的討論,其實反對派內有些人是要不得的,應該淘汰的。後來有人成了叛徒和背叛了。例如梁幹喬,他是《我們的話》的領袖、黃埔軍校的學生,他沒有要求統一,托洛茨基的信沒有來之前,他是反對統一的。托的信到來,他就不敢反對了。他想在統一內做一個領袖。但統一大會後沒有被選出來做成中央委員,於是統一大會後,他跑到南京去見蔣介石。梁幹喬是右傾主義的具體例子,還有其他人都背叛告密了。統一會議後,所有的領導幹部均被捕了。陳獨秀和我也應該被捕的,我住的地方已被揭發。那天拘捕了六、七人。一位托派同志機緣巧合下得到訊息知會我,才即時離開,所有文件統統丟掉,還想方法告訴陳獨秀,要陳戒嚴在家,不要到別的地方去。所以陳也沒有被捕。但新選的委員會成員幾乎都被捕了。那時我們是非常狼狽的!什麼都丟掉了,另方面,又要想辦法救援被捕的人,要找錢和關係。所以非常痛苦,陳獨秀不能出門又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因為被捕,其他的,特別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人都害怕,便離開了,故此很混亂,一直到1931年8月,我們幾個人都很痛苦,
到了1931年九·一八日本佔領了東三省,1932年2月28日日本佔領了上海,因日本侵略,中國爆發了廣大的民族運動----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人已經少,陳獨秀和我及另外一位中央委員又臨時組織起來,成立臨時機關,我們想辦法弄錢,出版週刊《熱潮》,又把所有組織和黨員重新組織起來,到學生和工人中活動,因有公開的刊物,可以公開辦,主張言論自由,要武裝抗戰,支持二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日本。我們的刊物有很大的影響。一般的群眾和共黨內部的人也看了。中共對日帝的侵略採取最荒唐的錯誤政策,不是抵抗日本,而是要保衛紅軍,擁護蘇聯,連二十九路軍都不支持,這就是王明時代的政策。
我們編輯托洛茨基的《中國問題》和《無產者》給他們看。在戰爭時期,上海有幾個中共支部,這個領導層看到我們的刊物了,是透過我們的同志,他們亦曾說托洛茨基的理論是對的!他們反對對托洛茨基派造謠。這時期,我個人忙得不得了,要寫文,又要出席會議、支部會議、跟他們談話,跟黨的人談話,因陳獨秀不方便。他年歲大了,沒有太大活力。經過很多次的談話,把上海黨部和幾個淮南區的支部、滬東的和滬西的支部十幾個幹部,全部說服過來,變成托洛茨基派的幹部。他們底下有很多工人支部,像浦東有十幾二十個工人支部的,就把最大的支部爭取過來。像郵政局、煙廠、電廠等都爭取過來。所以,上海托洛茨基主義就代替了斯大林主義。我們托派成功地領導上海的工人運動、罷工遊行。1932年10月15日我們全被捕了,是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陳獨秀不舒服,我代陳獨秀主持會議,會議到中段,大批警員包圍了,把我們六人拘捕。我們有一印刷機關,有兩油印工作的也被捕了。那次被捕了約十人。陳獨秀的秘書被捕了,此人叛變,被捕就供出陳獨秀的地址。淮南區支部和滬東區支部的幹部被捕,楊樹浦區是最大的工業區,在上海東面,滬東區整個委員會被捕了。從北京來的一批托洛茨基主義者如劉家良,到上海工作也被捕了。1932年4月我們被捕到1937年戰爭爆發,是托洛茨基運動差不多停頓的時期。所有幹部統統被捕,被捕幹部有30人以上,這個打擊最狠最大。在南京審判,不過審判是做宣傳,所有的報章刊登我們被捕了。托派的一個工業基礎,從黨爭取過來的,但是我們被捕了,那些幹部被捕了,大家失去聯繫。在法庭上我很嚴厲的公開反對國民黨。我的演說,報章摘要登出來。就是公開反對國民黨,用共產主義來改變中國問題。這是一個最廣大的宣傳。在監獄組織了托洛茨基主義小組,常常跟他們講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
(十一) 抗戰爆發後恢復工作
從1932年被捕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沒有中心思想情況下衰落。1937年8月的中日戰爭爆發,國民黨不能不釋放政治犯,共產黨已經投向國民黨。不能不釋放托派,所以我們從監獄釋放出來。我是最後釋放的。因國民黨一個領導人最仇恨我,因我在法庭攻擊國民黨太厲害,想把我處死。不過監獄長向司法部請示,司法部長認為不釋放是不能的,最後把我釋放了。我從南京監獄出來就到上海,開始要恢復組織,恢復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組織,剛好有其他監獄釋放來的同志,就集合討論要恢復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又通過抗日政綱,選出執行委員會領導機關。繼續出版刊物,還是秘密的,因抗日後情形稍微變化。國民黨不能完全控制我們,1939年,出版公開刊物《動向》和出版托洛茨基的書,我們有一批朋友,由陳碧蘭介紹我到南京結交一批朋友,這批朋友後來變成我們的同情者。 有一位曾是國民黨轄下當官,很有錢的,思想左傾,到日本讀書,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又一朋友是我們的老共產黨員,經這朋友,他變成我們很好的同情者。另一關係,一銀行家曾參加五卅運動的,他們都很同情和幫助我們。所以得到這三位朋友的幫助,出版托洛茨基的‘The Revolution Betrayed’《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名《蘇聯的現狀與前途》)。後來又出版《俄國革命史》三大卷,是幾本厚厚的巨著,還有很多小冊子,也是托洛茨基寫的。沒有大出版商是不能出版的。像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因要翻譯和校譯,出版又花費很大的金錢,大出版商不願出版沒有經濟效益的書籍,沒有前人的經驗,革命的書籍是出版不到的。所以,這幾位朋友籌集資金,我們找鄭超麟和王凡西翻譯,給他們生活費負責翻譯。翻譯好就出版,很快,時間約一年多,就把托洛茨基的巨著出版了。都是朋友的幫助。
我在革命前,接觸的人非常廣泛,在革命失敗後,有許多教授、知識份子最先離開,對這些知識份子很反感,他們從前要見我們都是見不到的,要入黨不容易的,革命失敗,他們最先離開。所以,革命失敗後,走到另一極端,我們很孤立。被捕的時候,陳碧蘭很苦,得不到幫助,只有幾個老的黨內的,也離開了,被捕時有第一個女兒和懷有三、四個月的身孕。我在南京跟別人不同的,我們是政治犯。我帶有馬克思主義的書,全是譯文,有俄文的書,托洛茨基、列寧寫的都有。監獄長不敢干涉我們,別人也不可以。所以有時間讀書,在監獄五年,整日讀書研究。什麼都看,朋友來看我,問我要什麼,就是書,所以朋友把各樣的書送給我,我的牢房就是一個小型圖書館。我看列寧、馬克思、恩格斯的書,尤其看他們的通信,他們只要利用得到的人,他們就利用來幫助運動。有些人跟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跟列寧通信的並不是革命者。我覺得我們有點過分幼稚了,覺得我們孤立不對。所以要改變我的態度,不要走極端。釋放後,陳碧蘭介紹的朋友都跟他們見面,亦接受訪問,得了一批朋友來幫助我們的運動。從這批書的發表,刊物的發表,是運動中的又一發展,從1938-1941年日本戰爭,珍珠港事件開始,我們的運動有新的發展,在各地方,北京、重慶、浙江、廣西、把舊有關係恢復過來,有新的發展。事實上,出版一大批的書有利發展影響,我也寫了一批小冊子,寫關於抗日的小冊子,西班牙革命失敗的小冊子,奧地利革命失敗的小冊子,對托洛茨基和蘇聯的情況有廣泛的影響,也公開出版了。
日本戰爭後完全變了。日本進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以,從前在租界上活動比較方便,租借是壞,但日本更壞,進入上海後,恐怖和隨便捕人殺人,像希特勒進入歐洲。因此我們領導中心同各地方的關係統統斷了,不能通信。隨後,日本進入北京、山東、廣東、廣西、武漢,大半個中國都被佔領了。我們的組織受到同樣的壓迫,加上我們在上海有五個幹部被捕了,他們擔任重要工作。於是,上海的組織就完全被破壞了。他們被捕,還要營救他們,我們對同志有責任的。所以,非常狼狽,幸好有些同情者,可以給他們一點錢。中國的監獄人員可以賄賂,可以找關係,所以我很狼狽,剩下的覺得上海不可留了,跑掉了,如劉家良跑到溫州,其他同志都跑了。剩下幾個人、陳碧蘭和我,同志要求我離開上海,大部分同志可以到其他地方,但我仍留守上海。有5、6個年輕人,我把他們組織起來,開一個訓練班教育他們。
這時候,大夏大學和之江大學的教授朋友,他們不大反對共產黨,在革命時代是有一點同情的自由派,由朋友介紹認識,到大夏教學,之江大學原來在浙江,後來遷到上海。因我沒有教育證書是不能教學的,和美國一樣。我現在做教授,用我的名字沒人請的。不提出哪國的學位來,是不能教學的。雖然我做過教學工作和有質素,但是不能提出來的。他說:沒關係,改一個名字。我就改名陳松濤。他說,陳松濤在北京大學當過教授,不過現在不願意用他的真名字了,因日本統治有危險。校長聽了後說,用真名危險,隨便用什麼名字。所以我就用假名陳松濤教學。
教中國通史、中國歷史、有時教西洋的文學發展,又講哲學。事實上,是講歷史唯物論。不用馬克思主義名義,因為有各種學生,我是用那個意思講馬克思主義,講中國通史、哲學、西洋文學史,有些普通學生不懂,覺得我很有學問,有左傾分子,聽懂我的話,說陳教授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下課後,學生來教授休息客廳找我。“陳教授,能到你家訪問嗎?”我說:好的。就這樣一批左傾的學生到家裏來,就跟他們談,後來爭取了一大批學生,有些是斯大林派的,後來轉變了,就是做教授得到的結果。
1941、42年開始,到1945年,做教授,展開同情網,結交一批同情者朋友,也是朋友介紹的,又跟他們講馬克思主義,他們是聯合的和激進的,所以我結交更多的朋友,有同美國做生意的商人。這時期的我,活動範圍不能到廠區,而是學生、大學生、一批自由派的、激進派的商人。這對後來很有用處,和平後,1945年8月戰爭停止了。同情者朋友就問,用彭述之名是有危險的。當時,寫文章不能用彭述之,學術上、哲學、歷史的文章用‘歐伯’。所以,同情者和自己同志叫“歐伯”,現在還是這樣。他們問:“歐伯,現在和平了,戰爭沒有了,你要做什麼?想做什麼?”我說,第一要出版雜誌刊物。出版刊物一定要錢,他們說,事情大家商量,並籌集了十條金條,大約五、六千元。他們說,要辦就辦最好的。我們很快恢復組織,重新建立領導機關。因做教授,有一批學生,通過學生,又有其他革命分子,所以組織發展很順利,有些老同志在工人中工作,1946年5月出版《求真》。《求真》是最漂亮的刊物,同情者做監督印刷,做得很漂亮,知道文章內容很好,刊物的封面也要一樣的好。他做經理,把刊物辦得最漂亮的。那時我忙得要命,寫文和組織,還有劉家良(他後來死在越南)的幫助。我自己曾有一本《求真》,在越南丟了。我們的雜誌一開始就暢銷,因為水準高,不是用彭述之,用陳人白。我們的文章有水準!我們宣傳托洛茨基思想,並不是拿托洛茨基的名字放在前面,內容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所以雜誌影響很大,初期約4、5千份,報攤和書店可以買到,所以影響就大。隨後,陳碧蘭辦《青年與婦女》,是她私房錢搞的。她得到一批青年人幫助,主要對青年人談婦女問題,所以是有另外一種影響的。我們的刊物使各地方有些組織,孤立的、個別的同志,他們看《求真》,全國到處有賣,知道是老歐辦的。所以他們就寫信來,把全國各地方的孤立組織串連起來。個別的人寫信來,也串連起來,所以很快恢復了全國組織。1948年,我們的黨員團員約四十人,不過我們有很多同情者,使我們的影響更大,因《求真》是戰後有名的最好雜誌,連蘇聯大使館也要。國民黨有許多所謂左派也要雜誌。所以,是托派新的發展。出版了不到三年,在1948年8月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到了高點。我寫了《黨綱》草案,劉家良起草了《組織原則和方法》草案,在會前發給各地組織討論,在大會上都通過了。大會通過將原來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改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以下簡稱「革共黨」)。1948年,毛澤東的中共跟蔣介石的內戰展開了。這時,國內局勢,對托派來說,危險是一天較一天高。

(十二) 被迫南下再出國
到了1948年12月毛澤東的軍隊已經攻打到長江的北岸,要進攻南京了,離上海很近,我們非常受威脅。毛澤東的中共是斯大林主義的黨,如果不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黨,沒有問題,我們合作好了!斯大林主義的黨特別仇視托派,可以跟任何反動派合作,就是托派不一樣。故此我們考慮到這個問題,改變政策,否則我們全部要被毀滅或監禁,像蘇聯的托洛茨基運動一樣,蘇聯沒有托派存在,全部被關在集中營,所以我們開緊急會議應付時局。
中共一定勝利,因蔣介石太腐化,對中國大陸,我們採取什麼立場?我們支持中共所有的革命措施,我們批判他們機會主義的政策,是我們的態度。另外,我們的黨員、團員要加入共青團,加入青年團,加入工會,不能獨立工作。在上海成立臨時委員會,同黨員聯繫,政治局則轉移到香港去,有同志在上海出名了、許多人認識的托派要轉移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人再調到上海,這是我們的安排。我和陳碧蘭、劉家良都是政治局委員,還有尹寬,他不願意離開上海,所以他被捕了,現在還在監獄。我們到了香港,是我們不能不離開,我們一定被毀滅。毛澤東要是得到我,不會放監獄內而是要絞死的,或送到莫斯科去,給斯大林作為一個禮物。
1948年12月,我們離開上海。在廣州住了個短時期,當時廣州組織還有幾十個人,中共的軍隊向廣州進攻,我們只好離開廣州到香港。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中國大陸差不多20年。同時是在蔣介石的國民黨統治底下,托洛茨基運動是一個不同的時代。
從廣州、大陸來到香港的人合起來,大約還有近一百人,我們把香港的組織推動起來,在香港出版刊物《第四國際》,我們幫助做教育工作。開始不錯的,我們黨員團員有學生和工人,我們幫助做教育工作,所以看來有發展的希望,但是另一件事情又來了。兩個同志做印刷的被捕了。跟著,有一位姓謝的同情者是銀行工作的,一個很好的人,是我們在上海影響的,他大學畢業,很有知識,英文也很好,他沒有加入托派,所以他調到上海一間銀行做會計主任,很高的地位。我們要接收國外報刊,我們自己地址不便,同情者說:我來給你們接收。所以他就接收《第四國際》及其它的郵件。托派中央機關到了香港,當局有偵探,也可能是斯大林黨告密!香港政府是最厭惡托派的,因托派常常領導罷工,例如在船廠、大紗廠等,托派在領導,我們的同志是領袖,所以香港政府很敏感,知道我們來了,就想方法要對付,要迫害,所以花力量檢查我們接收的外國郵件。有兩個人被拘捕,十幾人被捕了,有些釋放,有些被遞解出境到澳門或內地,跟著這事情發生後,他們知道彭述之在香港,他們用盡方法找我。他們不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但是根據接收報刊的同情者,有時到我住的地方去,就跟蹤他。警員有技術的知道他去這個地方,當局要來搜查這地方,幸好我事先知道,趕快搬到另一家去,也是朋友家。果然,一兩天後,那間房子被搜查了,兩同志也拘捕了。過一、兩個星期,搬去另一朋友家,又有跟踪,那便衣偵探來包圍,來調查,我只好又搬。大家就說,在香港是危險,連我們組織也是一個負擔,所以大家建議離開香港到越南。我們的同情者是陳碧蘭的親戚,幫助籌旅費到越南去。
1950年初到越南,住了年半。因是法國殖民地,非常反動。我用假名在越南生活沒問題,碧蘭和我教學,我們的女兒也教學,教中學語文、中學英文。生活是可以的。1950年2、3月,越南有托派組織要到胡志明佔領的越南區域去開會,劉家良也去,途中被越共拘捕,不幸死在獄中。我們又有危險了,加上北京老朋友告訴上海的同情者,說毛派知道我們在越南,要我們當心!因在越南要對付我們非常容易,只要一把手槍就可以了。越南常常打死人的。所以我們又要離開越南。香港同志給我們籌旅費,買船票到法國。到法國的時候,身上只有50美金,不過,我們希望國際上會有幫助。我們到了法國,正是第四國際召開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前,我們是六月到,七月末到八月開世界第三次大會。我是第一次直接參加國際會議,也參加了國際的領導機關。我們二十四人到歐洲,我們只有三人,有二十一人在法國。
(十三) 參與國際的領導工作
我參加了世界的托洛茨基組織領導層會議,初期還沒有分裂。後來分裂了,1953年,尤其是54年分裂。我們參加美國加農所領導的反巴布洛的鬥爭,我們捲進去了,因為我參加國際委員會的,在國際委員會工作差不多有十年。在這時期,我是主張統一的,我還存有文件和信件。不過那時候,巴布洛派也不願統一,英國希利也不願統一。我在這方面跟他們鬥爭,要統一。到了1962年,約瑟·韓生(Joseph Hansen)來到巴黎,1962年娜塔利亞·斯道娃(Natalia Sedova)托洛茨基夫人在巴黎去世。我才第一次見到韓生。在以前,我有通信,是給加農的,我寫了兩封很長的信給加農,有時候是給杜勃士。我就統一的問題寫了一封長信給加農,我認為要統一。在1963年韓生同勞斯·道遜(Ross Dowson加拿人),到我住處直接談。這中間有很多的障礙,不過我是堅決要統一,後來是統一了,1963年6月在羅馬開了統一會議。我是代表中國的革共黨(RCP)的。陳碧蘭都是國際上前線人,參加國際的領導機關工作,而且干預了國際上很大的是非問題,我們有意見,是代表中國支部的。我們對古巴,我有兩個文件,還有一個是原草案。我對阿爾及利亞,寫了一篇文章,是批判希利的,同時我支持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的一些意見。在隨後關於拉丁美洲的游擊戰爭,我是單獨一個人反對國際執委會的,在1968年,我們代表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干預國際托洛茨基運動。
當我們離開香港的時候,組織已受了很大的打擊,多位同志幾次被捕,驅逐出境。不過,他們還繼續工作,繼續出版文件,出版不定期的刊物,香港主要的政治意見還要靠我們幫助,我們寫的文章,如我在第三次世界大會上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他們出版了,作為我們革共黨的立場,此後他們對於農業集體化,也有他們出版的文章評論。1957年有一個‘大鳴大放運動’,他們也出版了文章,也有他們的立場。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他們有他們的意見,我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關於人民公社,我是批判社工黨兩個領導人,史瓦貝克和佛蘭克·格拉蘇斯(中國名字李福仁),我是批判他們,也批判中國的蘇達同志,他們都想反駁我,因此,我在1960年寫了一個重要文件《關於中國局勢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The Character of CCP and its Regime),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政治分析文件,一個綱領文件,外國都出版了,香港也出版了。對於文化大革命,我們寫了很多文章和訪問,不過這不是我們的同志翻譯出來,是明報月刊翻譯出來。香港同志還出版了《嚮導》叢刊,不過不定期,有時幾個月出一次,但是他們繼續工作,還維持了一個組織。他們是不斷地出版一些刊物、小冊子,他們是受壓迫的,雙重壓迫,香港政府壓迫托派組織很厲害,香港斯大林派的壓力。從前大陸的國民黨政治機關、銀行、商舖、產業,中共接收了,它有成千上萬人在香港,因為有錢,工會也給他們把持了,所以斯大林派的壓迫,同香港政府的壓迫合起來,我們的同志簡直就透不過氣來。所以有些同志消極了,少數同志想做,做不出什麼,就是出版文件刊物,從前留下來的人越來越少,現在都50歲以上,是替我們做工作,是我們在40年代影響的,經過三十年,那時他們20歲左右,現在變成了50歲以上,也疲倦了。同時他們在香港也要生活。所以,我曾經說過:“慷慨殺身易,長期奮鬥難。”我的親身經驗,一個革命者被捕了,慷慨激昂被殺不是很艱難,我們有成千的共產黨員,都是慷慨殺身的,但是要長期抗爭就十分難。因為革命者也是人。如果在革命過程中被捕,甚至槍斃,沒什麼,我自己就經歷過。在南京準備死,我寫信給父母和陳碧蘭,說是應該做的,最後為運動犧牲,我一點沒有感覺痛苦,因已決心抛出去,後來沒有死,就知道革命家是艱難的。
(十四) 香港同志的處境和工作
1948年從大陸避難到香港的同志,現在算來,二十六七年了,他們在大陸,差不多都有十年歷史,這些同志都經過了三十五、六年的鬥爭,他們要生活,又要工作,還要想方法弄錢來出版,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跟美國完全不同,比起香港同志,美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是很舒服了,那不能比那種艱難困苦!所以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是最艱苦的。他們工作堅持到現在是很艱難的,大家認識到,那樣的條件,美國現在的老同志,不過一兩百人。香港一些同志,幾十年了,所以我們是要體諒他們,不過我們總是要工作,這樣會有衝突。我有上百封的信,我現在還保存著,加拿大有同志的信,批判他們,鼓勵他們,提出建議。1968年我們到日本旅行,我和碧蘭在日本住了半年,香港派同志見我們,更多知道香港的實際情形和過去十幾年的情況,我們從日本回巴黎,寫了一封信給全體同志,要他們積極工作,現在的世界情況有很大的變化,我們建議他們籌一筆款,出版書籍,出版刊物,我們說,香港的青年,請你們活躍起來,因當時歐洲和美加有個青年激進運動潮流。像美國那些年青人反越戰,就是那個時候。他們籌了錢,把每月有的一點錢拿出來,籌了幾千元,準備要辦一個刊物,但很吃力,有錢,還要寫文章。編輯的人,寫文章的人不夠,他們又停下來。到1970年香港出了一個新的月刊《70年代》,這月刊是香港的青年激進化運動,當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這是一個新的青年運動,我們香港的同志很難影響他們,我們建議寫的文章,他們寫,但是不能夠影響他們。例如王凡西,他接觸他們,還不能夠影響,他不能吸收任何人加入我們的運動。1972年2月間,香港《70年代》雜誌二個成員到巴黎訪問我們,後來又有一批十幾人到來。他們一來便知道我的真名彭述之,他們是從外國的刊物上看到的。所以他們就問我許多問題。一青年李X明,第一次寫信給我,說他在香港是很重要的一個負責人,我答覆他許多的問題。我同這些年青人大約有一年書信往來。跟他們談話,他們提出蘇聯的問題、中共的問題、全世界的問題,為什麼蘇聯是一個官僚獨裁的專政?為什麼中共又是一個官僚獨裁?所有的問題,我都給他們答覆了,有時談很長久的。最後被我說服了,他們本來是無政府主義者,第一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再進一步是托洛茨基主義。所以,這批人1973年回香港,當中著名人物是回港組織「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革馬盟)的吳仲賢,不幸中年癌疾逝世。
因年青人膽子大,他們不怕,頂多坐牢。老的同志不同,拘捕會遞解出香港,到澳門或大陸去。年青人是生長在香港,英國政府不能迫使他們離開香港,最多關起他們。所以這批年青人反對香港政府,示威遊行。他們敢於公開說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所以,從前老同志不敢說自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年青人不管,香港的報紙就知道了,托洛茨基主義者就是這班人,報紙常常登載。從1970年開始,我們向他們建議,把托洛茨基以前的書籍重新出版,拿到書店去賣。首先拿到《七十年代》的書店寄售,它當然想賣,所以我們有一大批書,托洛茨基主義的書再版。像《俄國革命史》,像《中國革命問題》,現在又要再版。這些書籍印出來是公開賣的,所以托洛茨基主義的影響就擴大了。一年多兩年,他們出版《十月評論》刊物。托洛茨基主義者、托派運動在香港等於半公開。香港政府也不像從前的壓迫,共產黨是公開的,為什麼托派就不能公開?托派在英國是公開的,在倫敦是公開的,為什麼托派在香港就不能公開。所以,我們現在的活動比較公開,半公開的,兩個刊物和書籍出版。我們可以公開地代表托派去演說,由這批年青人去復興托派運動。《十月評論》已經出版了快兩年,知道他們很積極、盡力的做。我們的書現在是公開出版,《十月評論》上有我的名字,將來還有一些新出版的是我寫的。他們登載我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等文章。他們要出版陳碧蘭的訪問記和回憶錄。這就是香港現在的情形。在香港的組織有幾十年,從1940 年左右,我們香港有組織,但是從來不能這樣的公開,我們出版刊物,從前也有的,都是秘密的。最近一年多,我們的書公開出版,刊物公開賣。這倒是新現象,也可以表現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也是一個發展,香港的組織雖然很小,但是組織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因為所有斯大林主義統治的國家,從蘇聯到東歐、北韓、北越,沒有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香港,我們還有一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而且這個組織,最有鬥爭的傳統,這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十五) 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立場
關於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產生的思想基礎,我們就要檢查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對中國大陸所採取的政治立場,對於大的事變,它的政治立場是怎麼樣,才可以判斷托派起了什麼作用。我們可以用幾個大的事件做一個基礎,做一個標準來做判斷。
第一個時期是從1929年到1949年這二十年,托派活動在國民黨最反動的統治底下。第二個時期,就是從中共奪取政權以後,到現在二十六年。我們要分開來講。在國民黨統治底下,有什麼最大的事變呢?第一是‘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東北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本進攻上海都是大事變,對於中國的民族命運有關聯。我們採取什麼態度,中國怎麼辦?我們出版刊物,我們有文件、有宣言,我們的態度是分析日本佔領中國,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政策的結果,也是第二次革命失敗的結果。所以我們宣傳這個基本觀點。日本侵略,我們要武裝對武裝,應該要武裝人民來對抗日本的侵略。為了這點,要求國民黨應該給人民有自由,沒有自由,怎能夠活動呢?所以我們提出的政綱,就是我們的共同要求,為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這種專制獨裁,只有幫助日本,因他控制了人們的自由,所以人們要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人們要有公開的武裝,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此,農民、受壓迫的人們在一起,幫助農民得到自由,改善生活,因這是全民族的問題,為了實現這些自由,要有一個國民會議,要有一個普通選舉的有全部權力的國民會議,把這些自由活動結合起來,這就是我們的共同綱領。我們用這個共同綱領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的專制獨裁。這些綱領和宣言等,在當時都是有文件發表或登載在報章上的。
托派的運動也是上述同樣的兩個大時期,在上述第一個時期,首先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佔領東北三省,和1932年1月28日日本進攻上海,我們當時採取的立場,是號召全國人民組織和武裝起來抗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同時批判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我們提出由國民會議來解決重大的問題。
第二是1937年8月13日,日本軍隊全面進攻中國,這是繼續從前佔領東北三省一樣,繼續擴大,日本侵略是很重要的事件,對中國的國家命運很重大的一個歷史性影響,同時對整個國際也是。托派的政策是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支持抗戰,抵抗日本戰爭,就是在蔣介石領導底下,我們在軍事上,支持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另一方面,我們批判國民黨的抗戰政策,是錯誤的反動的,它壓迫人民,不許人民自動的武裝,不許人民組織武裝自己,自由組織,不給人民有自由,所以我們提出召開國民會議,以全國人民普選出的國民會議來領導這個抗日戰爭。這就是我們基本的態度。我們現在看起來還是對的。後來托洛茨基也表示這個意見,與我們完全一致。當然,在這件事情上,托派有兩種錯誤的傾向。一派是陳獨秀,他從監獄出來,變了。在監牢,我跟他鬥爭,證明他的思想錯誤,在支持抗戰行動上表現出來。他跟我們不同,他也主張支持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這跟我們一樣,但是我們反對國民黨的抗戰政策不徹底,尤其對於人民繼續壓迫,人民沒有自由。陳獨秀跟我們不同,他主張不要批判國民黨,我們也無條件去批判蔣介石。他是右傾機會主義者,那時他已經放棄了革命的立場。他害怕批評國民黨。這就是我們的文件表明的,關於陳獨秀的我們有好幾個決議。第二個傾向,就是托派中的鄭超麟,也是個老托派同志和老黨員,他是另一個極端。他因為蔣介石領導的抗日戰爭,他說這個戰爭不是革命的,我們則說有進步性。他說蔣介石同日本天皇是一樣的,兩方面都是反動,所以他主張我們對抗戰應該採取失敗主義。這是極左的。這一傾向很危險,在那時候,如果在客觀上,我們是擁護日本人,贊成日本侵略,因為必須首先要打倒國民黨蔣介石,他已經領導抗戰,這樣就等於做漢奸、做叛徒。所以我們反對,我們反對這兩種傾向,我為此起草的決議案,是絕大多數同志支持的。所以托洛茨基的政策是正確的,也就是我們所代表的。後來,在日美戰爭發生的珍珠港事變後,王凡西又是個失敗主義者,我也批判了,我們批判他,尤其劉家良最多文章批判他,他也是一種極左派。因為日本進入了中國,我們怎能夠對日本戰爭我們要採取失敗主義。我們採取失敗主義等於幫助美帝國主義。對這件事情我們是正確的。有很多文件,爭論得很厲害。結果,陳獨秀離開了托派。王凡西和鄭超麟也出來組織一個小組織。所以托派分裂了。不過,他們出去的人很少,幾個人。這是第二件大事。
第三就是和平後,托派對於和平後採取什麼立場?和平後,我們的政治立場是反對國民黨的專政,人民要自由,我們重新提出要有國民會議,解決國家的問題。《求真》同《青年與婦女》都發表這些意見,托派的政治立場是正確的。

最後,是國民黨同共產黨的內戰,引起共產黨後來奪取政權。我們起初批判共產黨機會主義政策,它等於投降,在中日戰爭中,它投向國民黨,它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介石這個領導,沒有重要地批判,所以我們批判它。和平後,共產黨還想跟蔣介石建立聯合政府,這是機會主義,和平後,情形很好,中共如果是個真正革命的黨,它可以很快的發動全國的工人農民走向政權,但是要跟國民黨合作,直到蔣介石把周恩來這位國共和談代表趕走了,才逼得毛澤東增加反抗,因蔣介石已經發表宣言,要拘捕毛澤東、朱德。我們批判這些。另方面,我們攻擊國民黨發動內戰,犧牲人民,這就是這時期我們對兩方面的批判。我們主張共產黨應該直接奪取政權,組織蘇維埃,這是我們的立場,我們認為國民黨應該打倒的,這是我們的立場。但是在這時期,我們托派有一錯誤。我們的錯誤就是,因共產黨用這樣純粹的軍事手段,不發動民眾,不能夠得到政權,原則上是對的,但是我們忽略了一點,就是第二次大戰後造成的整個國際形勢,特別是中國的局勢,是非常的特殊,所以中共雖然實行機會主義,它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走上了政權,我們後來檢討,我們對這一點,沒有估計到。這是我們的一個教訓。關於這一點我還要說的,就是在國民黨統治二十年當中,托派對於重大事變的政治態度和政策。我們現在來回顧,我們是對的。共產黨就不同,是機會主義的,一時是冒險主義的,所以,這與我們不同。有一個問題,為什麼托洛茨基主義正確,不能夠成為一個群眾的黨,領導工農走向政權呢?這是一個歷史大問題。我寫了小冊子解釋,就是托派在國民黨底下,被壓迫得非常厲害,例如1932年,陳獨秀和其他的同志被捕,在上海的,在全國的基礎上,我們當時在城市內的基礎,尤其是在上海工人中,我們可能很快的發展,成為一個大的黨,但是陳獨秀和我被捕,所有的幹部30幾人被捕,所以沒有辦法。這解釋了托派不容易發展,是受各個時期統治者的壓迫破壞太厲害。
(十六) 對中共統治政策的批評和我們的立場
第二件事,是毛澤東派走上政權後,托派的政治主張,在這點上,我們也要根據那個大的事變來看問題。起初是一般的,我們對毛澤東的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我們怎麼樣看法?第一,他是個機會主義者,斯大林派,為什麼能夠奪取政權?什麼樣的客觀原因?什麼是它的主觀原因?以及這個黨當時的政策,它的組織上政策,它的措施,以及它的前途。最後,就是我們的態度,這必須要有一種很嚴肅的分析。關於這方面,我在1951年11月做了一個很認真的研究,寫出了《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這是我給第四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國的托派同志是完全贊同的。我在這個文件內就做了分析,認為中共能取得了政權的客觀和主觀的原因,一是蔣介石政權的絕對腐杇無能和崩解,二是美帝最後抛棄蔣介石,三是中共力量在內戰,尤其是抗戰中的壯大,四是蘇聯對中共的援助(詳見十月書屋出版的《彭述之選集》第3卷)。跟著,我指出它的前途有三個,多半是東歐國家的道路,就是走向變態的工人國家,這是斯大林主義的表現。事實上,毛澤東是跟著斯大林當時的東歐國家的道路走的,我指出這個前提部份。我們的態度,我的報告後面提到,我們支持毛澤東政府所採取的一切正確的措施,同時,我們指出他們的不夠徹底,我們指出應該沒收土地給農民,沒收所有資本家的財產歸國有,沒收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財產歸國有。
另一方面我們指出,工人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完全是被官僚控制,我們主張工人農民兵士都要組織蘇維埃,來管理國家,然後才能建立一個健康的工農政府,工人和農民的政權,這就是我們的態度。我們這個態度很清楚,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關於這一點,我在1954年給瑞士一份托派的報章寫了一篇文章,我更簡約地叙述了我們托派的政治見解,在這篇給瑞士的托派刊物發表的文章中,我更具體地批判和分析,我們一方面支持中國政府反對任何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要摧毀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參加抵抗,這是我們的態度。要有一個真正的工農兵的蘇維埃政府,我第一次指出,中共如果不走這條道路,而走東歐的道路,將會有一個政治革命,這是我1954年第一次提出來,是我們托派的意見。
第二件重要的事件,是共產黨在1955年開始農業集體化,要農民參加生產合作社。關於農業集體化,我們支持,但是毛澤東的做法,我們反對。因他強迫農民參加。那時香港的托派同志,寫文章批判這件事情。我們表示這是一種列寧對農民的態度。1957年,毛澤東發動大鳴大放運動,就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我們一位同志寫了一篇文章指出:一方面,如果它真是要解放人民的思想自由,這是對的,但是毛澤東不是這樣,他是要利用這個大鳴放來查出那些反對派,引這些反對派連同中共自己的黨員說出他們的真心話,說是「引蛇出洞」,然後加以打擊,當作右派,拘捕了幾萬人,開除了幾萬黨員,所有批判中共的人都受打擊,我們認為這是個陰謀,事實是如此。這是我們對這件事的態度。第三大的事就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這些是中國事件中最大的事情,那時有5億農民,要他們一下子參加公社,這使全世界都震驚了,全世界的輿論都很驚奇。因為這實在是非常重大,在歷史上是沒有的。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但在我們托派內也有人贊成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是史瓦貝克和李福仁,中國有蘇達同志是贊成的。他們支持人民公社,不加批判的擁護。那時候,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也很煩惱,形成二派,由紐約和洛杉磯兩地的成員所分別代表。所以,杜勃士就要求我寫一篇文章。我寫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批評人民公社、農業集體化,我根據列寧、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以及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俄國的歷史事實和經驗,東歐的經驗,我全部的做了一個檢討,批判毛澤東的這種人民公社是一種冒險主義。我從理論上,歷史的經驗上,根據俄國的先例,給毛澤東一個批判,給人民公社批判。這種冒險主義必然會失敗,我預先指出要失敗。例如,公共食堂,我說這是行不通的,這是起碼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懂得的,物質生活落後,怎能夠把家庭完全不要,吃飯到公共食堂?就是美國革命以後也辦不到!還要等一段時間。這是非常幼稚的,沒有知識的,一定會瓦解的,公共食堂要取消的,那時還沒有取消,當我說這個問題時。後來,沒有公共食堂了。原來公社是一個失敗,後來又恢復到生產合作社。我相信我這篇文章,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對這個問題最精細、最正確的分析。這也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觀點。後來,事實證明,我們的分析是有預見。對落後國家,托洛茨基主義應該研究。所以,這篇文章刊出後,把史瓦貝克和李福仁兩人打垮了。所有的同志支持我們的意見,紐約的同志社工黨的領導是完全支持這個見解,而且給他解除了一個麻煩困難。其他的國家,像日本的Yamayiqi,他就最贊成我這篇文章的分析。當然,沒有人不贊成托洛茨基主義的意見。第三件,最後的一件是文化大革命。我給中共黨員的公開信,在明報月刊刊出,還有許多文章講解文化大革命。我在1967年2月16日《給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一封公開信》(見同上書)中,提出一個鬥爭綱領,我們的態度非常明顯,我們反對毛澤東用這種辦法排斥異己,排除反對派;打倒了劉少奇,林彪又來了。這就是我們正確的立場,我們批判反對派劉少奇,但是我們指出劉少奇有的政策,比毛澤東是有建設性的,代表溫和改良的。我們支持這個溫和派改良派,同時批判他不足夠,這就是我們的態度。像我們對俄國的赫魯曉夫批判,我們支持他的非斯大林主義,但另一方面,我們批判他不夠徹底。最後,我們反對批林批孔運動,我們的《十月評論》有大量文章評論這些事件。我分析,研究中共的歷史是很重要的。關於批林批孔,是毛派的作為,涉及一些中國重大的歷史問題。
對於中共這個政黨和政權的分析,我寫了一篇《關於中共的勝利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見同上書)這是比較全面的分析。雖然不像托洛茨基寫的《被背叛的革命》那樣詳細,不過,一般是那樣一個新的分析。這也是因為史瓦貝克和李福仁,寫了文章,他們認為毛的黨,中共,不是斯大林黨,毛的政權不是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政權,中國實行了純正的革命。他們是把中共美化了,這就是一種投降毛澤東主義的思想,這是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起初在社工黨裡,他們的文章發表使得社工黨的領導層很麻煩,因為他們不很懂得中國的情形,不知道怎樣答覆他倆人。所以杜勃士要求我寫篇文章講解。所以我就批判史瓦貝克和李福仁,完全是根據他們的文件來批判。在托派來說,是對毛派、毛政權和托派的基本政治革命綱領的一份文件,是最基本的。我們現在根據這個綱領,視為對毛派的政治革命綱領。
總而言之,這是一份很重要的托派文件。因它表示托派對中共的政權和前途,托派的基本的政綱,提出政治革命,表現托派是非常有原則的,根據馬克思主義,不是隨便反對和隨便贊成。像托洛茨基提出蘇聯要有個政治革命,他是根據理論和事實的分析,從這點上說,我們是一樣的,我們繼承托洛茨基。
指出托洛茨基運動在中國所經歷的,這四十六年,托派對於中國問題的政治主張、政治分析是有文件寫出的,還沒有另外一個國家的托洛茨基派有這麼多的文獻。因中國的事件發展得複雜,完全不同。一個斯大林黨掌握了政權,又是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所以,我們對整個運動的發展,做出了我們的思想貢獻、正確的貢獻,我認為我們是對的。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見到有人能否定我們或是有理據批判我們。此外,中國托派目前對於中國的問題是有有系統的分析,並堅持主張的。
(十七) 中國托派對幾件世界大事的意見
我們中國托派對於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對於世界大事的意見也有相當的貢獻。例如對古巴問題,我有兩個文件,1960、61年,卡斯特羅剛剛走上政權,我對他的分析。一方面,他建立的政府是革命的,但同時又有點危險,因為他國家太小和孤立。在美帝國主義壓迫下,可能要墮落,尤其在蘇聯的援助底下會官僚主義化。我這個分析,第一次我寫了篇文章,第二次,1961年我給國際委員會寫了一個決議草案,我們的分析,到現在還沒失效,事實上卡斯特羅是完全跟蘇聯走向官僚化。
第二件大事,就是阿爾及利亞,她同法國帝國主義,經過了多年的戰爭。我曾經發表過意見,提出阿爾及利亞應該走怎麼樣的道路?我這個政綱性意見包括在《白恩斯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往那裡去?》一文內(見十月書屋出版的《彭述之選集》第四卷)(註)。因這篇文章提到古巴問題,提到阿爾及利亞的問題,提到統一問題,這是我對國際問題比較重要的問題的文件。我對古巴的意見又重新分析,為什麼古巴走上政權和向社會主義道路發展,我說得更詳細。也說她的缺點。對阿爾及利亞有我提出的政治綱領。因為對阿爾及利亞,我認為,那時白恩斯是極左教派主義,所以,我就批判他。我提出一個綱領性文件,這也許很重要,對於國際問題,阿爾及利亞很重要的。
[註: 該文指稱 「阿爾及利亞的一切革命者必須團結起來,以現時獲得的政治獨立為基點,製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綱,再進而動員工人群眾及一切貧苦的農民繼續進行鬥爭,為撤退法國駐軍和取消它的經濟特權、為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和實現產業國有化、為爭取工農的民主權利,和建立工農兵委員會和工農政府而鬥爭,以此把阿爾及利亞推上社會主義道路----這便是我們對阿爾及利亞所應採取的路線,並以此為批評本.貝拉政府一切措施的標準,和鼓勵一切革命者去形成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黨,繼續進行鬥爭的方針。」(見該書第242頁)
第三件事就是關於智利1970年開始的革命,對於這個問題,我也有個重要的意見。我曾經寫了封信,給國際的執行委員會。我在1971年就主張智利要成立工農兵蘇維埃,否則,這革命一定會失敗。因為只有成立蘇維埃,才能夠使軍隊兵士,跟軍官隔離起來,才能避免戰爭。我在《導論》中也提到。這是托派對國際運動的貢獻。對於葡萄牙,我也有不同意見。我主張葡萄牙應成立工農兵蘇維埃,不能專靠立憲會議。不過,這事現在還在爭論。中國托派對於國際運動重要事變有其主張和分析。所以,我可以說,中國托派,從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從思想來說,是堅強的支部,我們特別的自豪。當然,我們的組織非常小,這並不是我們的主觀錯誤,而是一個歷史問題。托洛茨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創造了有系統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不能在蘇聯活動,蘇聯的托派同志們被摧毀了。所以,我們是可以解釋的。
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發展、挫折、失敗,處境是非常艱難的,但在政治上,是表示了托派的一種可以說是最深刻的,最廣泛的意見。政治立場證明是對的,在世界的托洛茨基運動裡面是不多的。
(十八) 回顧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工作
訪問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第二次革命中中共宣傳部的組織。當時宣傳部是我負責的。在1924、25年是沒有的,從前宣傳部是有的,雖然沒有機構,也就有個人負責,沒有正式成立一個機構。我回來後,因我被推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要我負責宣傳部,所以就建立了一個宣傳部的機構。是一種獨立的,單獨的,有一個負責人。我是宣傳部部長。組織了一個宣傳委員會,可以大家討論關於宣傳出版工作。因宣傳部工作很廣泛,要領導出版兩個刊物《新青年》和《嚮導》,我要負責。這些刊物是對外和對內宣傳。還有對內的教育工作和辦黨校。所以要有個宣傳委員會來討論。宣傳委員會就是我、瞿秋白、蔡和森。但是蔡和森後來去了莫斯科作代表。剩下我和瞿秋白,我們宣傳委員會有陳喬年秘書,我們開會討論。有兩份報紙和兩刊物,我是主編,陳喬年是助手。所以,我們主要工作就是出版。有黨校組織,很忙,沒時間教育,因革命發展像狂風暴雨般急速!上海五百黨員,連青年團員一千多些,一年後便一萬多。所以我們人手不足夠。教育工作做得非常不夠。不過,我們也做了一點宣傳工作。
第二個問題是我和瞿秋白。這問題很複雜,因有許多外國書籍,老是說彭述之與瞿秋白有仇恨、有衝突。我這個人從來不同人爭,我對於同志是採取一個正當的態度,我們同志間工作,政治上意見不同,也沒關係,可以討論。我是依照布爾什維克的傳統,我懂得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思想,我自己參加過。所以我是採取這種態度。我跟任何同志沒有成見,我看他的思想,看他的工作的成績表。對瞿秋白也是這樣。瞿秋白在莫斯科有一年和我在一起,他的俄文很好,比我強,但他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機會主義思想。1923年回國,和陳獨秀參加第四次國際代表大會一起回來。他回來,黨叫他編輯《新青年》。他寫了很多文章,但是他的文章有個很大的毛病,因我也懂俄文,他把俄文翻譯出來算是自己的,寫上瞿秋白的名字,我看不起此事,我認為不忠實,尤為重要的,他在上海大學當教授,他講唯物史觀,他把布哈林的那本唯物史觀翻譯出來,後來,翻譯本印刷出來寫的是瞿秋白著,沒有說是從布哈林的書翻譯的,非常不光彩。
(編按: 原有錄音帶說到此為止。憶述和錄音歷時15天,從1976年1月1日至同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