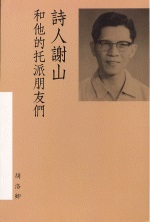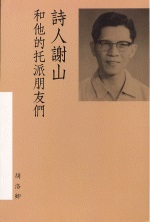
我是怎样写<诗人谢山和他的托派朋友们>的(转载)
胡洛卿
清明时节,是对先人的怀念。时间过得很快,谢山逝世十四年了!这十多年
来,我常常想着他的一言一行。
谢山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褔?」他怀才不遇,坎坷一生,是个不幸之人。可他却认为:有幸生长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伟大时代,看到「沧海桑田三度见」(指: 1. 抗日战争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蒋介石统治;3. 斯大林主义由盛至衰,苏联解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大饱眼福!祸与福是相对的,没有祸,也无所谓福。所以常说:「生在福中不知福!」
谢山去世前,已被折磨得百病纠缠。莫说高血压、心脏病、甲亢等顽疾,就是肺病一种也够受了。在「阶级斗争」的年代,病了得不到休息,手上拿着几张不同病症的假单,也要「班后学习」。而所谓「学习」,是下班以后,干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这样的「学习」,比一天正常生产还要辛苦得多。但这不算「上班」,没有工资,没有劳保。短短几个月,把他的身体摧垮了!左肺功能丧失,右肺也不健全。靠这不健全的右肺,供养全身血液,加上其它病症,日子很不好过。能活到七十多岁,是够坚强的了。可一旦失去了他,实难接受。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也无力抗拒。在朝思暮想之下,我写了《谢山小传》,当初只是寄托哀思而已。后得友人鼓励,要我补充完善,还主动给我打字。我写呀写呀,写了十多万字,写不下去了。初写的万余字,还有点满足感;后写的十余万字,反而不满意,不知怎样写好谢山这个人物……。
回忆过去,免不了勾起满腔心事,思潮起伏,难以控制。一些亲人出于好心,劝我辛辛苦苦几十年,时至今日,应该过几年安乐的日子,何必自寻烦恼?况且名人传记多得很,谁来看你这个无名小卒?算了吧!我力排众议,还是我干我的。
有时意外的事影响深远,坏事会变成好事。由于《谢山传》写不下去,想赴港求助。不料申请探亲无理受阻,大半年未办成。究其原因,是办事员故意刁难之故。于是我趁此人不在,另找一位年青人。他照章办事,给我一纸申请表,我当即填好给他。他问:「单程还是双程?」我一气之下,申请单程。心想:单程去港,以后来往自由,不再受此窝囊气了!结果非常顺利(其实是正常的),很快批准了。初来港定居很不习惯──人地生疏,生活程度高,居住面积小,房租贵。但这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受歧视,办事公平合理,快捷妥当。我来港时已年过七十,在广州居住二十年,老人证也未领到。来港不久,只填了一纸申请表丢进邮箱,未几即寄来了<长者卡>,还有一大本指导性的书──各区政府机构、医院、警署等等所在地、电话号码,以及规章制度,办甚么事找甚么地方,一目了然。既来之,则安之,很快安定下来,断断续续写《谢山传》。
2004年,我应邀参加城市大学举办的「新来港人士座谈会」。当时《谢山传》写不下去,像一只小船驶离了岸边,在江中飘荡,到不了彼岸。在会上发言时,我以<有志者事竟成>为题,表示决心要把<谢山传>写好。后来我想到应该藉此机会把谢诗词介绍给读者,于是修修改改,2006年写成<诗人谢山>。
笔者向来对诗词没有兴趣。谢山每写诗词,我是第一个读者。我看不懂,他给我解释,我过后即忘。现在要写<诗人谢山>,实力不从心,只有苦思冥想,尽量从书本及后期留下来的信中找资料。
谢山做事认真细致,一般诗词的写作时间,只写年月,如加上日期,定有作用。有关东欧剧变等诗的含义,我是根据日期,翻看当时的资料写成的。我想:「虽不中,不远矣!」但是更多的诗词,我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好照搬,不敢妄加说明。
笔者向来做牛做马,不会舞文弄墨,所写的文字,看一次改一次,改来改去,自己也认不出来,找人打字也难。只好学计算机,自行修改。我不懂英文,记忆力差,要学新科技,谈何容易。幸得各方相助,老人中心大力支持,计算机出问题了,朋友、社工、义工上门指导,令人感动!在写《谢山传》时,也写了和谢山一起的朋友们。友人看了,认为没有必要。我删去了。后来想到:那些朋友已先后去世了,我是那个时代唯一的历史见证人,应该留下一些史实,于是又把它补了上去。最后定名《诗人谢山和他的托派朋友们》。
拙作得到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也是够幸运的。谢山生前自编的<苦口诗词草>,罗孚先生在<明报‧岛居新文>专栏连续撰写了七篇评论文章。谢山的朋友王凡西老人剪寄给我,并说今人多不懂古诗词,建议我找人作注,以便吸引更多读者。我给罗孚先生写了一封感谢信,并请他笺注。罗先生欣然接受,要我提供数据。可惜我对诗词一窍不通,不知注释要些甚么数据,毫无办法,只好作罢,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但因此和罗先生有了联系,后来把拙作介绍给天地圗书公司,并得到艺术发展局资助出版,得以面见读者。
得与失是相对的,因为失去了谢山,才想到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我不相信命运,但自认这十多年来都碰到好机会。能完成这部十多万字的著作,也是很意外的。我想:如果谢山有幸多活几年,我不会拿起笔来写些什么,更不会写书。那时,精力和记忆力都衰退了,给我打字的朋友也老病了,我写的字,过后自己也认不出来,更没本事去学计算机。「幸而」谢山去世时,我只有六十多岁。虽然记忆力差,还能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有时半夜睡醒,想起甚么,拿笔记下,以免第二天忘了。如果在大陆,拙作是写不好的,不能畅所欲言,畏首畏尾。就算写了,也无法面见广大读者。即是说:如果那次探亲申请不顺利,就不会来港定居,也就没有《诗人谢山和他的托派朋友们》这本书的出版了。所以受了挫折,不一定是坏事;把坏事变好事,就靠各人的努力与机遇了。现在看来,还应该感谢那位刁难我的干部呢!他改变了我此后的历程。
2010年4月
转载自2010年的《文艺评论》